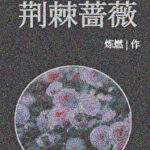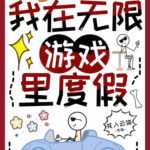事情的開端是從我死後。
那天,勾魂死者為我的魂魄戴上枷鎖。
“我哥呢?”茫然四顧我竟然沒有看見我哥的影子。莫不是他沒有死?不!我記得被扔下河的時候他就再我邊上,比我還早閉上眼睛。
勾魂使者不解的看着我,“這裏只有你一個人的魂魄。”
和我一起死的哥哥卻沒能見到他的魂魄,我不懂。但是,那時候一直沉浸在被白憲宗背叛的痛苦之中,以至于我究竟是怎麽被帶到枉死城的都不知道。
這是一座巨大的城池,高聳入雲的城牆,血跡斑駁的鐵門,城裏什麽也沒有,沒有樹木,沒有房屋,只有人擠人,全都聚集在城門口不斷的喊冤。
如這裏的名字一樣,枉死城,這裏的人都是枉死的,陽壽未盡還不能投胎。哭號聲不斷的在耳邊萦繞不絕,我抱膝蜷縮在安靜蹲坐在一邊,深思着為什麽白憲宗明明說了要救我卻把我推進河裏?下水之前他眼裏那抹哀傷又是怎麽回事?我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這種感覺一點都不真實。爹娘會很難過吧?我和哥哥都死了,誰給他們養老?
我咬牙不讓自己哭得跟城門下那些冤魂一樣,因為我覺得那很狼狽、無用也可悲。
“你不想回人間嗎?”在枉死城裏呆了快三十年的周敏芝主動跟我打招呼,“聽說只要能從這裏逃出去,到了陽間之後,地府的人就不會管你了。畢竟陽壽未盡。”
我雙目無神,緩慢的擡起了頭,“要回去做什麽?他都要我死了,我還回去做什麽?”聲音有些沙啞,怕是再多說幾句我就該哭出來了。
周敏芝靠在我邊上,平靜的說,“真不想回去了?來這裏待了這麽久,還是頭一次見到不想回陽間的人。”
“真羨慕你,能活到死的時候都無牽無挂。”陳秀兒靠在我右側的牆壁上,她仰頭看着那高聳入雲的城牆,眼神有些空洞,“真想回人間,變成厲鬼殺了那莫雨寧,要不她又該禍害其他人了。”
“莫雨寧?”我好奇的重複着這三個字。
陳秀兒嘤嘤的哭了起來,“那時候我哭着求她不要打我,可是她卻裝作沒聽見的樣子,一邊打還一邊笑着,我哭得越大聲,她就笑得越大聲。”明明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她為了不讓自己看上去那麽狼狽,于是強扯出笑容。眼淚不争氣的流下,此時她的笑容才更讓人心疼,“你說,”陳秀兒哽咽,她用手背不斷擦拭一雙淚眼朦胧,“為什麽有些人看見別人痛苦會那麽高興呢?我們的命就不是命嗎?”
周敏芝輕拍陳秀兒的後背,安慰她,“看開點吧,死都死了還能怎麽樣?我再等個兩三年就可以投胎了。喝下孟婆湯,生前那些委屈也都不記得了。”她說得灑脫,可是卻眉頭緊皺心事重重的樣子,“好想再見他一面啊。最後跟他說了那麽狠的話,他會傷心吧。”周敏芝重重的嘆了口氣,“他為我都做到那個份上了,老早就知道他的心意了。只是怕自己越是溫柔,他以後的日子會越自責。”
我們仨就這樣并排靠在枉死城的城牆邊上,我一度以為我們要一直等到陽壽已盡的時候。
“你怎麽……死了?”那本該是從我眼前走過的魂魄卻在看清楚我的模樣之後,詫異的停頓了。
我茫然的擡起頭,“你是誰?”
荊笙苦笑,“如果你不記得,那麽我就重新介紹。我叫杜荊笙,想和你度今生。”那時候他眉目如雪,清雅動人,腦海裏浮現出“陌上人如玉,公子世無雙”的句子。我從沒有見過這麽漂亮的人。
“可我已經嫁為人婦了。”我遺憾的說。
他溫柔一笑,拉着我的手,“從你死的那一刻開始,你就自由了。所以,成為我的妻子好嗎?”
“為什麽?”我羞紅了臉,不懂荊笙眼裏的激動,他看着我的模樣帶着一眼萬年的滄桑,他究竟經歷過什麽我全然不知。就覺得前世一定在哪裏見過他,或許我該懂得他的悲傷。
“因為,我愛你啊。”不知道他是抱着什麽樣的心情對着剛剛才認識的我說出這樣的話。
我放開他的手,“對不起,我不認識你,我們這才第一次見面,你這麽說未免也太突兀了。”
荊笙垂下眼眸,原本墨玉般的眼睛失去了光澤,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做錯事情了,我竟然讓那雙那麽漂亮的眼睛蒙上了陰霾。沒來得及開口道歉,荊笙就恢複了精神,“那我們第二次見面能這麽說嗎?”
我蹙眉,心想他一定是瘋了,然後沖着他搖了搖頭。
“什麽時候可以告訴你我愛你呢?”荊笙沒臉沒皮的問。邊上的秀兒姐和敏芝姐一臉的嫌棄啊,怎麽看荊笙都是登徒浪子。
我眨巴眨巴眼睛,“不知道。”
“那就等你也喜歡上我,喜歡的無法自拔的時候。”荊笙扯開笑容自信的說。
後來蹲在城牆邊上的人從三個人變成了四個。再後來,我們四個覺得城牆邊上太吵了,于是逆反其道,朝着枉死城的深處走去。
走了很久之後我們遇見了段楓,他也在往城門相反的方向走,于是我們就順路了。
這一路我們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經歷和死因說明白了,大家也就心照不宣了。原來都是可憐人,我們沒有做過什麽壞事可是我們死了,那些害死我們的壞人卻在人家逍遙快活。湊在一起的時候,我們都忍不住語言激烈的咒罵那些人。
遠離那些哭嚎聲,我們走到一處比較僻靜的地方。我一直以為枉死城只有荒蕪的一片,沒有任何的植物也沒有任何建築,可是那平地而起的屋子打破了我之前的想法。
沈玲緩緩從屋子裏走出,一身白底紅花的彼岸花旗袍,剪裁得體,把她襯得愈發的婀娜多姿。
“為什麽這裏有房子?”周敏芝不解的問,“我在枉死城都快三十年了,從來沒有見過任何的屋子。”
“我建的。”沈玲自豪的說,“別以為枉死城什麽都沒有,我就不能平地起波瀾?這地上不是還有土?”
“好厲害啊。”我和荊笙異口同聲的說完還鼓掌了。
沈玲沒有不好意思,她挑眉得意的問我們,“要不要拜我為師啊?”後來想想,她這德行和神婆簡直一模一樣。
我想了想,然後一口氣答應了下來,還要在枉死城待這麽久,閑着也是閑着。
“好啊。”沒想到荊笙居然又和我異口同聲的回答了。
沒認識多久的人居然能有這麽好的默契,真是相見恨晚。于是我們倆就一起拜了沈玲為師,學習法術的時候沈玲和荊笙直誇我天資過人,荊笙還私下教了我他的法術,這也奠定了之後我成為黑衣人的實力基礎。
和荊笙的感情一點一點的發生變化,他總是寵着我,給我說各種各樣的故事,開始的時候有些厭煩,因為經歷過白憲宗的背叛,他主動接近我的時候我特別的讨厭。但是他教我法術的時候必須接觸。
說不上什麽原因,我總有預感一定會有離開枉死城回到人間的一天,所以學習法術的時候格外的用功。
“如果我是你丈夫,你是不是就不會排斥我啊?”荊笙看着刻苦專研法術的我突然說。
我懶得搭理他,“你不是叫杜荊笙嗎?怎麽又變成白初泉了?”我以為他只是閑着沒事做,開玩笑而已。
一回頭荊笙卻一臉嚴肅的說,“我既是杜荊笙也是白初泉。真正的白初泉在十七歲那年已經死了,如果沒有他母親在身邊守護的話,他估計活不到十七歲,他死之後我附身在他身上,所以其實那時候你要嫁的人骨子裏的是我!”
“這笑話一點也不好笑。”他倒是說得輕巧,這故事編得可真夠曲折離奇的,誰會信啊?
荊笙一臉無辜,“可我說的都是真的。白家夫婦是餘豔和白岳霖,‘我’弟弟叫白憲宗,管家是白忠叔,伺候的丫頭是小花兒和阿秋……”
我驚愕的盯着荊笙,他比我早到枉死城這些消息只能是生前知道的,如此一說他也算白初泉。
“和你拜堂的人可是我。”荊笙正經的說,“雖然那時候我已經死了,可我求了那勾魂很久他才答應讓我跟你拜完堂再走的。”
“你真的是……”不管我如何的不相信,事實已經擺在面前了。
又是白家人,又是白家人,為什麽我就是不能擺脫白家呢?
而得知荊笙的身份之後,我只是鐵着臉,默默的說了句,“滾!”
那天之後我生了很久的氣,有兩個月都沒有搭理荊笙,最後還是他一個勁兒的追着我跟我道歉一直賠禮道歉,把天陰山的各種禁術都教給我了。
我本來就不是狠心的人,伸手還不打笑臉人,不争氣的我終于在某一天忍不住被逗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