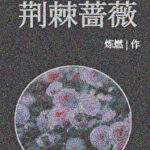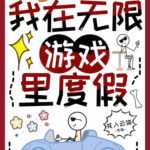自從兩宗大戰之後,此地靈炁逐漸平複,但山形地貌終究是遭遇了不可逆轉的損害,迄今依然還有些許空間裂縫,橫亘在空中,那是兩宗偉力也無法完全消除的板蕩之力,也是因此,這一帶山形之中,多是人跡罕至的高山大河,不過是數百年功夫,已是長成了許多鳥獸,在其中鳴叫跑動,自由自在,幾乎從未見過生人。此時見到遁光彙入,無不是争相走避,惹得林間箬葉索索,竹雞驚飛,還有不少落入一處長滿了雜草的院子中,沖着屋子鳴叫不已。
阮慈和朱羽子落入此間,卻是全然兩樣的感覺,只見這小院雖然年久失修,院牆倒塌,便連院中小池都已完全幹涸,只留一二滴水液在青苔上滾動,似乎已有許久沒有主人打理,但在兩人靈覺之中,卻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象,那水液中散發沖天靈炁,俨然便是太一宮中、三生池水。此水又和時間川流中的液滴有所不同,那時間川流,乃是任何修士都可以靠近的所在,只是如今被時之道祖封鎖而已。但三生池水,卻蘊含了別樣精粹,非是正統嫡傳,對這般傳說中的靈液,也是只有聽說的份。傳聞此水一旦離開三生池,便會自行生出靈性,倘若未得太一君主許可,便是滔天大能,也根本無法馴服。
朱羽子在宇宙中游走萬古,只怕也是第一回 得見三生池靈液,此時目注小池,不知不覺淚如泉湧,跪倒吟道,“碧羽山前得點化,始知大道啓鴻蒙。三萬劫來心未改,宇宙尋道至君前。”
她周身氣韻卷動之間,似是幻化出無數求道險阻畫面,全是朱羽子走遍宇宙,尋找師門蹤跡,歷經艱險、參悟道韻的畫面。那淚水一滴一滴,落入池中,砸得青苔破碎,逐漸和靈液溶于一處,點染出無窮畫面,逐漸往朱羽子飛來,阮慈在旁看了,心道,“真是小裏小氣,不會只給這麽幾滴三生池水便打發了罷?上次我還裝走一瓶呢。”
她猜是因為自身在旁,時祖不敢現身,不過方才已用那段往事逼迫過了太一君主,方才有招來相見一幕,一招也不可兩用。便轉身飛離小院,才剛跨出院牆,便覺身後迷霧騰起,任何神識都無法穿透,再看四周山巒,不知何時也隐于迷霧之中,四周白氣團團,便如同阮慈和僧秀前來尋找時間瘴疠時一般,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進不讓進,去又不讓去,阮慈也就随遇而安,在這片唯獨沒有被迷霧湮沒的竹林之中盤膝而坐,只覺那時間道韻如同潮水一般漲漲落落,似是發生了些許難測之變,又好似世界線正在經歷輕微的改動,只是因其和阮慈、琅嬛周天等幹系都不太大,因此她感應并不強烈。
也不知過了多久,白霧中鞋聲跫跫,僧秀從小院方向走了過來,笑着對阮慈合十唱喏道,“慈施主,許久不見。”
他看似依舊是築基修為,但此身只是化身而已,阮慈感應之中,氣勢淵渟岳峙,深不可測,竟是數百年內便有了元嬰境界。可想而知,其定然是在時間川流中穿梭來去,在過去積累了深厚修為,只是回到現在破境而已,又或者時之道祖也賜予其《陰君意還丹歌注》一般的機緣功法,這才能在極短時間內将實力提升到如此境界。
此中曲折,對低輩修士來說,可遇而不可求,但對道祖來說,卻是随手為之,哪怕連洞天都是随手點化,更遑論其餘?阮慈并不詫異,回禮笑道,“我還當你已經被點化為洞天呢,想要鎮壓門戶,非有洞天不可。人家水祖的瀚碧宮說不定就有兩大洞天坐鎮。難道時祖并不培養你,反而要認下朱羽子麽?”
僧秀含笑道,“師尊也曾讓小僧擇選,究竟是被他點化為洞天菩薩,還是自行修行,小僧選了後者。”
阮慈贊道,“僧秀師兄好志氣。”
被點化為洞天,修為難有寸進不說,便如同九幽谷素陰白水真人一般,只能奉命行事,主見絲毫無有。不像此時,僧秀的修為是自身苦修而出,固然也欠下太一君主深深因果,但還有再修其餘大道,或者等太一君主超脫離去之後,接手時之大道的合道希望。而且對周天大劫這棋局,其秉持時祖意志之外,也可保留自身的立場,不過代價便是放棄唾手可得的長生不老,還有那翻雲覆雨,左右周天局勢的大神通。僧秀怡然一笑,在阮慈對面盤膝坐下,道,“貧僧也不過順心而為,循因果行事。得師尊收錄門下,固然是恩同再造,但無垢宗引我入道,施主幾番施以援手,這些恩義,又怎能不償還呢?”
若要償還,那自然便是要在周天大劫之中,為琅嬛周天出力。僧秀其實已做出自己的選擇,阮慈和他相視一笑,二人不再多言,思緒各自從腦後飄然而出,碰撞之中,異彩紛呈,無需言語,便将己身觸碰道韻的中中體悟坦然分享,這正是彼此對道韻都有一定造詣,修為也大略相當的修士之間,談玄論道常用的手段。只是阮慈在元嬰境界獨戰勝場,很難遇到敢于和她論道,又不怕被她道韻壓制的同輩。
僧秀心性純粹堅定,又得時祖垂青,在時間川流中沐浴修行,論道韻積累,勉強有和阮慈交流的資格。既然如此,雙方便都能獲益,不過僧秀尚且還不敢碰觸太初大道,只是觸類旁通而已,阮慈倒是從論道中汲取了不少對時間道韻的感悟。
二人論道已畢,見周圍白霧仍濃,阮慈便道,“你這師父,也實在是故弄玄虛了些,收徒用得了這許久麽?我又不是沒見過他,倘若不想見我,便讓我出去,倘若想見我,又何必如此矜持呢?”
僧秀赧然笑道,“師尊自有深意,我們做弟子的也不敢妄言,不過大師姐在外流落不計量年月,如今終于回歸,彼此定然也有許多言語,稍後待她全然重煉法體,皈依道韻,正身降臨此處,大約便可請慈施主入內相見了。倒不是提防施主,只是此時時間川流波蕩不平,三生池太一宮難免受到波及,界限有少許模糊,師尊又不許任何非本門修士靠近時間川流,如此也是為了護住慈施主,免得被道韻障礙驅走,對你化身有礙。”
阮慈原還奇怪,這白霧為何只是遮擋視線,對她和本體的靈覺聯系倒沒有什麽妨礙,聽了僧秀這話,方才釋然,又問道,“你平日修行,見太一君主多麽?他身邊有兩個童子,你可見着了?”
僧秀道,“黑童子和白童子甚是調皮。”
他拜入師門之後,直到修成元嬰,方才順流而上,離開下院,去到太一宮正體朝聖,在時之道祖玉像之下修行了不知多少年,方才被喚醒回歸。至于太一君主,将他接引入內之後,便不曾化身相見,但待僧秀卻說不上冷淡,不論是傳法解惑,還是增長見識,都有無形思緒道韻湧來,對僧秀可謂是呵護備至。到了衆人如今的層次,實則外相已是微不足道,一縷道韻,足夠傳神。不過僧秀入門之後,只顧着修行,倒并未有和太一君主說過什麽私話兒,偶然興致來了,便和太一宮中兩名道童嬉戲玩耍。
他本是一片禪心,出自天然,如今返璞歸真,待阮慈更加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笑道,“太一宮中門庭冷落,師尊似乎除我之外,并未收下入室弟子,那兩個童子很少見到生人,在我之前,見到的上一個生人還是慈施主,他們津津樂道了許久呢。”
阮慈道,“只怕還有許多弟子,都和朱羽子一般,先在外修行,其後才能拜入門中呢。”
時間修士,最能混淆因果,僧秀微笑道,“大師姐的确是如此,不過我聽師尊的意思,正是因為時間修士神通廣大,可以随意更易時間線,因此修士人數萬不能多,否則恐會加劇宇宙失衡。如今我們琅嬛周天博弈之勢漸成,衆方勢力共逐超脫之機,或許宇宙平衡,也會在此局之後重置,或許是重新獲得平衡,或許是徹底失卻平衡,便連師尊也不能肯定此局的結果。”
僧秀拜入師門這才多久,以他敘述,不過是在過去中度過千百年的功夫而已,因他不肯被點化洞天,也就還是受到壽元限制,無法在過去經歷更多,這些見識,或許便是時之道祖借助僧秀之口,說給阮慈聽的。阮慈也十分上心,點頭道,“情祖也曾對我說過宇宙失衡一事,但局勢已經如此危急了麽?此事難道真和諸多虛數大道的誕生有關?當真是本方宇宙的藩籬所在?”
僧秀俊秀的面容上俄而浮現一縷高潔光芒,語調也顯得高遠幽渺,聲音在若有若無之間,帶了奇妙道韻,倘若對時間道韻無有體會,聽到的便是毫無意義的嘈雜聲響。“此事便連情祖都不知所以然,唯有我師尊這樣橫跨兩個宇宙的修士,才能觑見其中關節所在。此事,并非宇宙藩籬,而是宇宙瑕疵,又和本方宇宙的至高意志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