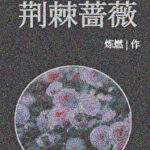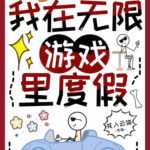阮慈此言一出,衆人當即凜然,都從馬儒生身邊逃開,雖然明知未必有用,但也各自使出護身神通,又分別凝神四處觀望,尋找念獸蹤跡。種十六來不及怄氣,牢牢扣住阮容素手,沉聲道,“留神!我感應中念獸在左前方。”
他雖然依舊看不到念獸,但感應中可查知危險方位,至于那福滿子,更可逢兇化吉,早就憑直覺遠遠離開念獸,周身浮動絲絲明黃之氣,正是福運、功德、氣運諸般吉祥之氣交織而成的護身之氣,令由癡迷幽怨之氣凝結而成的念獸天然便是忌諱不喜。
這兩人已算是衆人中的佼佼者了,但也僅能自保,難以克敵。要說對付這情念精魂,還是阮慈最為出色當行,一聲輕叱,運起那無名功法,身為未來太初道祖,自有一番威勢,長袖才剛拂出,道韻光華一展,那念獸便是尖叫一聲,松開馬儒生,往回便逃。
它身形本就極淡,一旦離開馬儒生,立刻便要沒入這南鄞洲上空無處不在的幽怨之氣中,此氣縱橫交錯,一旦被它逃去,只怕連阮慈也奈何不了它,恰是此時,王真人一聲微哼,揚手牽引來空中星光紛落,這念獸兩旁的雲霧全都被星光驅散,它一時無處遁逃,只得回首一聲尖叫,欲要引動四周癡怨之氣,一道攻向衆人。長嘴更是同時猛吸,像是想要從王真人和阮慈心中,吸走什麽情念一般。
這種情念層面的攻防,在實數中沒有絲毫體現,倒是癡怨之氣聚散,可在氣勢場中觀照出少許,阮慈對這二者都是夷然不懼,道韻反而附上那念獸襲來之氣,笑道,“就怕你不出手。”
道韻沾上念獸吐息,順勢向本體蔓延,畢竟它要通過靈炁向兩人心中吸走情念,也就意味着冥冥中定然存在一條通道,而道韻無所不在,阮慈只要認清此點,便可從通道中反向汲取念獸本源,此獸正是從情念中衍生而來,旁人無法奈其如何,在阮慈手中卻仿佛是大補之物一般。功法一轉,便覺得道韻修築速度更快了數分,将那本源之氣不斷煉化,那念獸根本連逃都來不及,哀叫聲中,再難維持化形,便是化為一大團濃霧,被阮慈鯨吞虹吸一般收入掌心,運轉功法,從容煉化。
衆人見她回轉,都是有些不信,種十六皺眉道,“這念獸死得也太容易了些,傳聞此獸最是狡詐,這會不會只是它的一個化身?”
阮慈将其煉化時,自然也能汲取一些識憶,聞言搖頭道,“這卻不是,若是它和別人交手,便是不勝,也可從容逃走,但它撞在我手上,那便是前來送死的。不過此獸乃是雌雄成對,這只雄獸力量較為弱小,大約只有金丹修為,神通也弱些。還有一只雌獸誕生更早,也更為狡詐,這雄獸便是被它派出,來試探我們虛實的,既然如今這雄獸眨眼伏誅,只怕它會更加謹慎,或許不敢出手,轉頭去找那兩個大玉修士也未可知。”
這念獸無聲無息間便将馬儒生攻陷,聽聞還有一只在外頭游曳着尋找機會,衆人臉色都是微變,種十六把阮容往自己身邊又扯了扯,沉聲道,“只有千日做賊,沒有千日防賊的道理,劍使可有什麽辦法能驅除此獸,或者至少是預警它的接近。”
阮慈也是心系阮容,對種十六也有些愛屋及烏,蹙眉道,“我自當警醒些,還有一法,便是将此舟遍布我的道韻,不過如此一來,你們生死也就在我一念之間了,你們可是願意?”
阮容自無不可,但除種十六、福滿子外,其餘人卻都有些躊躇,互相交換着眼色,也拿不出什麽更好的辦法,仲無量拿話岔開,指着馬儒生問道,“劍使看看他有無大礙?自從剛才那念獸離去之後,他便呆若木雞,好似受了什麽重傷。”
阮慈定睛看去,果然見到馬儒生腦海之中,一股新生念頭正和另一股遭受重創的薄弱念頭纏鬥不休,令其極為痛楚,全副心力都在調和心念之上,因此對外界毫無反應。她微微一怔,忖道,“這新生念頭,和大不敬之念截然相反,難道是道兵對道祖天然的崇敬之念?”
“此念遵循大道至理,天然占據強勢,此念一生,頓視‘大不敬’之念為異端,二者不能共存,總要放棄一個才好。馬儒生的大不敬之念卻又被汲取了許多,他……是了,他對此念,并無太多認識,只是受環境侵染,天生便有大不敬之念而已,既無執著,一旦被汲取一空,很難憑借己身再生出許多來和崇敬之念對抗。”
她伸手一指,道韻糾纏,順着那念獸剛才取食的傷口侵入馬儒生本源,将那新生的崇敬念頭汲走,馬儒生面上痛苦之色稍解,但阮慈道韻剛一離開,那崇敬之念便又生出,而大不敬之念則一直處于弱勢,難以滋生,阮慈也十分納悶,沖王真人微微搖頭,道,“恩師,我治不好他。”
王真人此身雖只有金丹修為,但神通畢竟不止,對馬儒生體內的交戰似乎也知之甚詳,點頭道,“你且先退出來。”
阮慈将道韻撤出,便見馬儒生體內那崇敬之念,經此壓制之後,反而似乎生命力更強,迅速将大不敬之念壓倒,馬儒生面上也是如癡如狂,不住喃喃念叨着甚麽狂亂之語,衆人能聽明白的也只有“上下有序、尊卑有別”之類的碎語而已。阮慈皺眉道,“我明白了,他是儒道修士……”
儒道最講上下尊卑,萬物秩序,大不敬之念本就和其道法天然沖突,也是因此,崇敬畏懼之念一旦誕生,便難消解,即使是未來道祖,只是簡單汲取心念,也無法拔除這念頭的種子,而大不敬之念一旦消失便很難再生。因此這鬥争注定是要以大不敬之念落敗而告終,只阮慈還不知道馬儒生為什麽這樣痛苦,她心中從無對任何事物的崇敬虔信,還未入道,便知道自己多數是本周天道祖的眼中釘,卻也依舊不肯屈從,便不知道要放棄心中的大不敬,遵循儒道,一心投入到對道祖的崇敬中去有多麽艱難。
王真人立在馬儒生身前,靜候片刻,方才點頭一嘆,伸出長指在馬儒生肩上點了點,馬儒生動作驟然一頓,面上現出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感激、怨憤、惆悵、解脫、不舍,諸般情緒交錯的複雜表情,将王真人看了一眼,最終仍是拱手一揖,身軀一陣抖動,剎那間化為萬千微塵,被風吹去,散在天地之中。
王真人袍袖一抖,淡然道,“此子被念獸吞噬心念,已經瀕于瘋狂,不能再見容于周天,只能先送他前往虛數,也免去他掙紮受苦。”
和念獸有關的種種博弈,不是這些修士能夠理解的,也只有王真人才能将馬儒生的變化完全看懂。不過阮慈已試着治愈卻告失敗,這一點衆人都是看在眼裏,仲無量反應最快,忙道,“念獸狡詐,還請劍使出手遮蔽飛舟。”
她顯然是在剎那間估量了阮、王聯手的戰力,知道這兩人可以殺死舟中所有人,不會遇到任何阻礙,想通了這一關節,那麽阮慈道韻覆蓋飛舟,對衆人的好處顯然遠遠大于壞處。
種十六、福滿子早知此點,更不會有任何異議,他二人一旦附議,那麽其餘人的意見也就無關緊要,只有附和一條路走。阮慈也不推辭,伸足輕跺甲板,道韻如水,從她裙邊不斷淌落,将飛舟表面包裹覆蓋,她有種奇特的感覺,仿佛自己在某一層面上和一氣雲帆本身蘊含的道韻達成一致,甚至彼此還隐隐有友好之感,這是她多次道韻對抗後,首次體會到道韻相融、相生之感。
至于舟中衆人,她的感應也更加清晰,一氣雲帆仿佛成了阮慈的又一個內景天地,衆人此時的氣勢、法力,阮慈心中都是有數,甚至連心情都能隐約感知。此刻自然多以戒慎為主,要再往深處去感應那些雜念,卻不是此時的她所能做到的了。
剛入南鄞洲境內,便有了這麽一出插曲,衆人均感此行不會這樣簡單,更好奇大玉修士來此究竟是為了甚麽。在原地稍微修整片刻,便又沿着感應追蹤了過去,越是往深處走,那如絲如縷的怨氣便越是濃郁,不過一氣雲帆有阮慈道韻包裹,所有怨氣哪怕只是稍一靠近,便被當成養分掠奪了過去,這幾日她道韻修築速度,竟要比在中央洲陸時快了五成。
也是因此,衆人都更加警惕,阮慈也在自己艙中修持功法,倒是無暇再去煩擾王真人。這般行了幾日,種十六忽道,“我已失去對那兩人的感應,定是雌獸報信,他們使用秘法,屏蔽了自身感知。”
阮慈神念之中,感應也是若有若無,但王真人神念已是鎖定其人,始終未曾丢失,那兩人似也有所察覺,不數日後,方位又是一變,衆人追攝而去時,卻覺一路上的空間裂縫要比之前頻密了許多,王真人道,“感應方位是互相鎖定,看來雌獸已和他們同行,利用南鄞洲內的地理,設法想要延緩我們的腳步。”
一氣雲帆乃是洞天靈寶,等閑空間裂縫并不放在眼裏,只是阮慈道韻并未煉入舟身,駛過空間裂縫時難免會有所散失,她只得收回道韻,改為灌注在阮容身上。
若說覆蓋舟中,衆人還可勉強接受,灌注身外,也就意味着阮慈對其人的掌控要更加具體,甚至連心念瑣事都不能瞞過。除卻阮容,衆人均感不适,仲無量道,“那雌獸此時和大玉修士同行,想來也不會到此,等行出這段區域,劍使便又可庇佑舟身,這段時日我等小心些也就是了。”
阮慈也是無可無不可,她将阮容護好便可,也不會因此特意去窺探什麽,此前庇護整舟時那模糊的感應,倒也罷了,具體到阮容一人身上,便是兩人親密,行事也要有度,這種事不可有意為之。
種十六、福滿子自恃其能,便是沒了遮護也不擔憂,其餘修士卻多少有些畏懼,便結了一陣,燃着清心法香,一同入定,摒除所有心念,這樣若是雌獸來襲,心念一吸,那人便會立刻驚醒呼救。阮慈也不知這樣做有沒有效用,不過倒是比甚麽準備都沒有要強些。她亦是感慨周天之中,各式各樣的危險真是難以防備,這些弟子氣運都十分強盛,便是遇到元嬰修士,只怕也不會沒有抵抗之力,但在念獸之前,便猶如幼兒一般,完全是任人采撷。還好各洲自有大陣防護,彼此相距迢遠,否則若被這念獸跑到其餘洲陸去,怕不是要掀起滔天禍事?
那大玉修士來此的計劃,似也被衆人擾亂,接下來十數日內,雙方都在不斷移動,但有一氣雲帆在,琅嬛修士自然要快上幾分,雙方的距離正在不斷縮短,彼方只能不斷變換方位,讓衆人在空間最不穩定的區域多航行一段時間,借此拖延。但雙方因果鎖定越久,距離越近,一氣雲帆的速度也就越快,此舟若被洞天真人禦使,可在數年內便橫跨大洲,從中央洲陸穿過迷蹤海和護洲大陣,來到南株洲。在護洲大陣之中,破碎重疊的空間根本是司空見慣,一氣雲帆尚且夷然不懼,更何況此處呢?
不知不覺,雙方的距離已是拉到了數萬裏內,不過是一氣雲帆半日的航程,此時舟速已是極快,仿佛是受因果牽引推拉,根本不用王真人輸入太多靈炁,衆人又有了方位變換過速的眩暈之感,已不能維持入定,阮慈心中微覺不妥,只怕被念獸尋到破綻,便去船舵邊尋到王真人,正要說話時,只見船頭前方突然現出一大團雲霧,王真人輕咦了一聲,剛要躲開,那雲霧卻仿佛是有意識一般,驀地張開大口,将整艘小船一口吞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