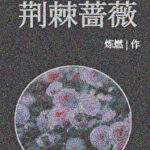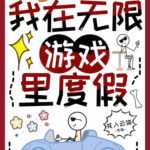若說氣運是宇宙中所有必然與偶然的統合,那因果又為何物呢?
阮慈心中仿佛分成了數個部分,一部分正凝神思索因果的本質,另一部分則冷眼旁觀,瞧着那四團氣運落往無窮遠處,甚而‘看’到了虛空之中,無數氣勢因此而起的争奪,雖說宇宙中有資格争搶這般道祖氣運的,不過是極小一部分人而已,但道争之下,無人能夠豁免,而洞天争鬥,又怎會不牽扯到低輩修士?這氣運雖只有四團,但攪動大勢,真不知要激起多少風浪,改變多少人的命運。便是阮慈此刻,仿佛也能隐隐看出每個方向之中,許多修士的因緣變幻,甚至是悲歡離合。甚而有一些從前已經發生,現在無從改變之事,亦是生出因果,和這氣運鏈接在了一起。
“這要比恩師給我演示得更加玄妙……但也不能說恩師就未能窺見這個層次的大道隐秘,只是當時我所知還有限,恩師或許只是為我稍解其中一二,更深的奧秘,還要等我到了上境之中自行探索。”阮慈凝望那白光去向,也是心馳神往,為大道玄奇感慨迷醉,又忽而暗嘆道,“宇宙奇觀,如此瑰麗無量,但我琅嬛周天修士卻只能坐困道韻屏障之後,便連洞天修士也不能破障而出,那大玉周天修士反而可以自如來去,洞陽道祖對我等何其不公。”
這念頭她早已有之,但怎敢随意念及?阮慈心中不知有多少大不韪的猜測,但也是深知自己在琅嬛周天之中,深受洞陽道祖道韻籠罩,便猶如處在其內景天地之中一般,便是有東華劍鎮壓身軀,若是本身修為太過低微,只怕思緒也經不住洞陽道祖一念探索,這才未曾多想。此時得了涅槃氣運,又是最為自由自在,神游大千宇宙之時,方才稍微放松警惕,忖道,“我身無洞陽道韻,本不能修道,卻偏偏得謝姐姐傳劍,她走之前更斬落天下劍種,真靈盡收劍中,這是為了護持不被各方滋擾,成功拔劍,将東華劍守到她回來之後麽?大概是的,但又并非全是如此,謝姐姐亦是要斷絕沾染洞陽道韻的真修得劍的所有可能……除了我之外,周天之中再無劍種,洞陽道祖可能想得到,在他道域之中,卻偏偏是一個未染道韻,可以随時随地離開琅嬛周天的修士,成為了這一代東華劍使?”
謝燕還在宋國大陣內躲藏七百年,這大陣究竟是為了困住她,還是阻擋所有身具修為者進入三國,阻礙她修行秘法,誰能說得清?能布下絕靈大陣的洞天修士,又是何方神聖,此時再看,角度已和從前截然不同,阮慈心中亦是暗嘆謝燕還的決斷,“怪道謝姐姐說自己是琅嬛周天萬年來第一流人物,她從南株洲上空離去之時,道體燒起靈火,和清善真人化身燒開通道時所燃火花一般無二,這定然也是一門秘法,清善真人用它來燒開空間屏障,謝姐姐卻燒去了自己身上的道韻。若是、若是她成功回來,那麽,東華劍不論在我手中,還是回到她手上,那都是沒有洞陽道韻的人,來當這個劍使。”
想要突破道韻屏障,哪有這麽簡單,阮慈從寒雨澤回來之後,已知如種十六那般,墜落出空間裂縫,落到周天屏障之外的琅嬛修士,也只能去到道韻香花所能鏈接的最遠處,根本無有可能自在周游。甚而清善真人這樣的洞天大能,想要走出周天,也要做好化身折損的準備,也是因為這化身已被斬落出來,和本體氣運并不相連,只有随着時間衰退的識憶,因此才能進入寒雨澤,否則,洞天氣運,哪怕只是一部分,也是寒雨澤無法承受之重,寒雨花将會完全凋落。寒雨澤便無法和此時一樣,封閉得這麽緊密了。
她上回閉關至今,依舊沒有大玉周天餘孽,乃至是救出阮容之人的半點消息,但見王真人等并不急切,也知此事或許已在氣運因果中露出端倪,再者此時還是以觀望那四團氣運為主,思緒稍一飛遠,便又集中回來,見到那四團氣運已飛向宇宙中極遠之處,連四周星數都看不清,這本不是她能望見的視野,阮慈甚至有一絲感覺,這氣運無論如何也不能在短短時間內便飛到如此遠處,自己正是借助了氣運之間極為緊密的聯系,在窺視未來某處的景象,甚至每一處氣運視野的時間,都未必一致。
她心中一動,暗道,“難道,這……就是因果?氣運是宇宙中所有必然和偶然的統合,因果便是宇宙中所有事物,橫跨時空之上,最為本質的那一絲關系,無論親疏厚薄,時之前後、空之遠近,所有聯系的統稱?”
這一念一生,只覺得那四團氣運猛然一顫,和她之間生出一條茁壯絲線聯系,再看周身上下,密密麻麻的因果之線,往外生出,卻是再不分修為上下,不似王真人和她展示時一樣,略去了許多無謂聯系,只有值得注意的幾條。以阮慈之身為圓心,往外生出無量因果,神念過處,随意拽動一條,心中便随之生出感應。譬如她身上那許多在有無之間,淡如無物的因果之線,便來自昔日被斬落的劍種,之所以在有無之間,便是因為謝燕還執她之手,斬落劍種,兩人誰也沒有說明要承擔這份因果,因此這份因果到底算在誰的頭上,且還不好說。此時或許無礙,将來兩人若有誰要收束因果,少不得也還要分說個清楚。
左右再望,有些黑色、血色線條,便是來自阮慈所殺之人之獸,還有些閃着光亮,顏色柔和的線條,則是來自友朋。只是她只能觀照自身,卻無法看到線條彼端的人物,想來終是修為有限,也沒有修過感應心法,只能大略猜測。
阮慈見了那些悅目線條,自然歡喜,又對一條粉色絲線三撥兩動,唇邊也挂起頑皮笑意,心道,“不知絲線另一端可有感應無。”
對那些負面因果,倒也坦然接受,點頭道,“該當的,殺得了你們,自然也承得了這份因果。”
又好奇想道,“因果之力,我已觑見,但無從取用,不知又該是誰給我呢?”
她隐隐已知,這三層只能借道祖之力凝就,涅槃道祖給了她氣運之力,又借助飛出氣運,領悟因果,知曉己身第十一階由因果鑄成,但七十二道祖之中,也不知誰願将因果本源贈她,這答案亦是只能由阮慈自己琢磨,答案不出,恐怕亦拿不穩這贈禮。
偌大機緣,換做旁人,只怕多少有些患得患失,但阮慈又怎是常人?不慌不忙,垂首思忖一番,唇邊已現笑意,叫道,“我明白啦,因果之力,跨越時空,可我的視野未必能跟着跨越,令我看到這一幕的,可不就是我本經《陰君意還丹歌注》的道祖,時之道祖,陰君太一!”
随她每一字說破,那四團氣運中的一團突然大放光華,落入無窮虛空中某處星辰,星辰微微亮起,只見通天長玉階,一節一節徐徐亮起,盡頭處一尊神像宛然而立,只等氣運落下,投入眉心,從上到下滾滾而落,将它一寸一寸照成生人,正是阮慈每每意修之時,所能望見的那尊太一君主!
在她身上落子的道祖,阮慈所知的已有三人,這其中要以太一最為隐秘,說來早至她還未入道以前,太一便已落下一子,只是連阮慈都茫然不知,此時想來,雖說她也依照《青華秘聞》打熬法力,但修行關竅,還是靠《陰君意還丹歌注》,那尊太一君主是她每回和青君相會的橋梁,這一子,豈不是要比涅槃道祖所落更早得多?
太一君主立于玉階頂端,對阮慈颔首微笑,兩人似是初會,卻又仿佛已十分熟悉,阮慈想道,“這般大的動靜,不怕引發洞陽道祖關注麽?啊,我懂了,對因果而言,時序并無意義,便如同涅槃道祖可以令果在因前一般。或許對旁人來說,這氣運才剛飛出琅嬛周天不久,要在無窮遠的将來,才落入太一君主手中,但有此一因,他便可在此時将果報予我。”
而那重重阻隔,無窮遠的空間,對因果而言,也是猶如不存,阮慈一步跨出,便走到玉階下方,與那氣運光團走在一處,又或是己身便是那氣運光團,眼前是無窮玉階,昏暗中可見玉階盡頭隐隐矗立一尊神像,這一步,不但跨出了不知其遠的距離,更仿佛還回溯片刻時間,回到了氣運剛落之時。
她每走一步,那第十一階道基便凝實一點,阮慈倒也不去想何時要到盡頭,只想着走出不長不遠的一段,得到她所應得、所想得,不多不少的那一份便可。至于貪欲、野望、謹慎、惶恐、自滿等雜念,早在氣運凝結時便置之度外,視為心靈中拂過的趣致風聲,心中随意逍遙之念,早已占據上風,拾級而上時,更是悠閑觀望星空,早将那距離、時間抛到了九霄雲外。
也不知過了多久,走了多遠,內景天地之中,那第十一階道基終于鑄就完全,天地之中風雲再起,阮慈只覺得小腹一沉,仿佛那丹田處的內景天地之中,多了一絲重量,輕如無物、重比千鈞,這又輕又重的矛盾感,便是此時身處某種玄而又玄的狀态之中,也覺得道體不适,如非此前得了幾番煉體,此時恐怕真要堅持不住,難以為繼。
這多出的一絲,便是因果之重,阮慈內景天地之中,哪怕是一草一木,此時都有了己身因果,與她緊緊聯系。這每一物單獨的因果,雖然單純弱小,但內景天地如此廣大,草木扶疏,所有因果算在一起,又是何其沉重,但也因此,那些誕生于內景天地之中的生靈,乃至之後可能被移居進來的妖獸,才有可能真切對外界施加影響,否則,無因果萦繞,固然無甚牽連,但在旁人看來,便也猶如不存,永遠不能和外界産生交互。只是其餘修士在金丹境中,尚且未能感受到因果重量,而她則在此時已有了領悟。
此時她已走到玉階頂端,那氣運光團再次落入太一君主眉心,将它照亮返生,從蓮座上步步行下,和阮慈相會,兩人目光相對,阮慈泰然自若,反倒是太一君主興味盎然,将阮慈上下打量,良久,唇畔現出一抹神秘微笑,對阮慈伸出手來。
阮慈并不猶豫,将手放入太一君主掌心,随他往蓮座之後行去,她已知道這第十二階,将會由誰來贈予,太一君主便是牽引她前去與那人相會,若無他相助,也不能成事。
只是,此時心中要厘清的是,這第十二階,她要凝練哪一樣本源之力——青君必然是助她凝就第十二階的人,但向她索求什麽,卻在阮慈自己,也只能由她自己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