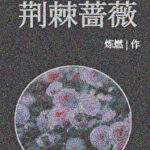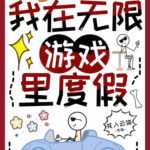那批苗木處在苗圃深處,已蔚然成林,雖沒遮天蔽日,也足以掩蓋陽光下的罪惡。
康昭沒有回複。
柳芝娴只能提高聲調,放慢步調,一路給老板講解。
何粵霖負着手,不時微笑點頭接幾句,一副專家視察的派頭。
希望只是她誤會了。
“小柳說話這麽用力,也不怕把一副好嗓子喊啞了。”何粵霖笑吟吟道。
柳芝娴忍着反胃的沖動,皮笑肉不笑,“前幾天碰上小車禍撞到腦袋,不瞞您說,現在有一邊耳朵還是不太能聽見,我自己感覺不到大聲,不好意思吵到您了。要不然我把別人喊回來——”
“小柳很怕和老板呆着?一味逃避在職場上可不是一個好習慣,容易流失機會,影響升職加薪。你去年剛研究生畢業吧,還需要多磨練磨練。我挺看好你的。”
柳芝娴一側身,不着痕跡避過他準備拍在肩頭上的手。
“職責範圍之內的事,我會竭盡所能做好,請老板放心。”
何粵霖毫不尴尬收回手,面上一派老練的從容。
前方便是柳芝娴去年親手培育的品種,講解不知不覺帶上本能的熱情。直到後背傳來另一個人的溫度,聲音戛然而止。
柳芝娴要閃開,何粵霖兩條胳膊反倒箍得更緊。
“小柳什麽時候也用這種聲音跟我說話就好了。”
“放手,老板您請自重!”掙紮中柳芝娴維持最後的禮貌。
“我不信你不懂我意思,我是挺喜歡你的。”
陌生男人的氣味壓迫而至,柳芝娴朝他肩頭後叫出來——
“小昭哥,你怎麽來了?”
聲音和眼神中的欣喜不像作僞。
何粵霖乍然回頭,女人掙開禁锢,小跑到來人身邊,竟然還有點小鳥依人的姿态。
老奸巨猾的男人只用一秒鐘便恢複常态,朝康昭伸出手:“這是保護區派出所的康所吧,久仰久仰。”
“你是……”
康昭沒去接那只手。
何粵霖自若地換上名片,“我是這裏的老板。我小孩剛好是令堂的病人,跟康所在醫院有過一面之緣。”
“是嗎,我媽媽的病人我不太清楚。”
“不知道康所來找小柳——”
“有點私事,看樣子還沒下班?”
康昭望了柳芝娴一眼。
柳芝娴忙如實相告:“正給老板介紹新培育苗木的情況。”
“說起來我也算半個同行,如果不涉及商業機密,是否也能有幸聽一聽?”
何粵霖巴結還來不及,哪敢再說不。
柳芝娴換回平常語調,定心把剩下的講完。不知不覺把康昭當成潛在的小白客戶,每講完一段就會尋找他的眼神,等康昭稍微有反應——有時點頭,有時複述或提問幾句——才繼續下一部分。
日頭西斜。
何粵霖說:“今天周五,小柳要回城裏吧?要不要順便載你一程。”
“來鎮上大半月還沒去過外公家,周末準備去看看。”
“那……”
康昭和柳芝娴站一塊,怎樣看都像一對璧人,沒有半點挪步的意思。
何粵霖暗咬牙槽,負在身後的手狠狠攥緊,腕骨處熬出幾根暴怒的青筋,憋屈都咽心裏,臉上堆起客套的笑。
“行,不打擾你們,我先走一步。”
何粵霖獨自飄離小樹林,夕陽之下影子越來越瘦小,似乎還有佝偻的錯覺。
柳芝娴肩膀垮下,松了一口氣。
“你剛才叫我什麽?”康昭盯着她的眼睛。
“……有嗎?”柳芝娴僵硬躲開。
“妨礙你們好事了。”康昭略帶嘲諷。
柳芝娴一愣,瞪他:“你這人嘴巴怎麽這麽毒。”
康昭忽然攬住她的腰,一手捏着她下巴,迫使她直視他。
“毒你還給我親?怎麽沒把你毒死?你把我叫來,難道不覺得我比他更危險?”
柳芝娴給鎖得死死的,身體有意無意擦碰,擦燃難熬的心火。
那雙眼如密林深潭,再多盯一會,怕會心甘情願溺亡。
她總覺得,康昭先比出的還是那晚虎口掐頸的手勢。
柳芝娴說:“你不一樣。”
下巴上力度有所松緩,但康昭還沒放開她,輕搖一下,“哪不一樣?”
康昭聲線沉啞而立體,放低聲時更加富有磁性,比起質問,這句話更像撩撥。
柳芝娴說:“你是我自己選的,發生意外,我自認倒黴。”
……好一個“自認倒黴”。
康昭無聲輕笑,“那看來你今天運氣不怎麽樣。”
氣息交織,迫人心慌。
柳芝娴不掙紮也不迎合,任他擺布一般。康昭莫名想到英勇就義的女革命者,唇角一彎,松開她下巴,手還停在腰際,“如果我不來,你打算怎麽辦?”
他挑釁地掐了一下她的腰。
柳芝娴喃喃:“大概就這樣辦吧。”
半空驟然傳來滋滋聲,千萬道水線噴薄而出,細雨灑在他們身上。
自動澆灌系統啓動了。
康昭反射性松開她,還罵了一句什麽。
柳芝娴手中不知幾時多了一只小而薄的遙控器,朝他晃了晃。
“能停下來嗎?”眼看四周沒有一塊幹燥的地方,康昭用手臂擋着眼疾步外走。
柳芝娴跟上,“不能,得澆夠一定時間。”跑到半路,又喊道,“不過我真的要謝謝你。”
康昭停在苗圃入口,淡藍色夏季警服已然半濕,狼狽不已。
柳芝娴也半斤八兩,但相比最壞下場,這點小落魄算不得什麽。
“我是說真的。”她強調。
康昭留着極短的板寸,若不是一身警服,看起來痞裏痞氣的。可當他眼睛盛滿笑意,整個人就溫柔起來。
他顯然瞪她一眼。
柳芝娴不懼反笑:“你怎麽找得到我的?”
“從樓頂一眼就看到,才多大點地方。”
他示意旁邊三層高的小樓,柳芝娴這才注意到他肩上還挂着個望遠鏡。
比起他以腳丈量的大山,基地的确小巫見大巫。
康昭說:“你真去你外公家?”
“對,我得上去收拾一下。”起碼得換身衣服。
“我去縣城,順道載你。以後不要再坐黑車。”
柳芝娴皺鼻子抗議,“如果西瓜李的順風車也叫黑車,那你的是什麽車?”
“警車。”
“……”
說罷,康昭轉身走向大切諾基。
宿舍在三樓,柳芝娴上到走廊時不自覺往樓下瞄了眼。
男人站在車門的夾角裏,正脫掉警服裏面的背心,赤-裸脊背在夕光中泛着誘人的麥色,肌肉舒張,靈活有力。
三兩下套好一件純黑T恤,康昭似有所感,忽然一甩車門,朝小樓轉身。
柳芝娴趕忙縮回去,匆匆進去換衣收拾。
長褲和平底鞋換下,柳芝娴一襲長裙,戴一頂寬邊帽,拎一只不大的行李袋,飄然下樓。
柳芝娴坐副駕,上車也不摘帽,帽檐無形阻止交談,只有色彩熱烈的唇和下巴暴露在康昭的視線中。
沒有音樂,康昭默默開車。
外公家的桐坪村在南鷹鎮和縣城中間,村口離縣道還有一長段距離。
外公還沒到,康昭陪她等。
扶手箱有一只葉子疊的三角錐,跟粽子一樣。柳芝娴早在上車前注意到,一直沒機會問。康昭拎過頂端的梗,扔到她懷中。
“給你。”
口吻跟動作跟昨晚扔玫瑰如出一轍。
“這是什麽?”柳芝娴小心翼翼端詳。
“毛毛蟲。”
“啊——!”
小粽子飛到康昭腿邊,他彎腰撿起,又笑着抛回去。
“到底什麽啊?!”柳芝娴活像捏一只張牙舞爪的小龍蝦。
“打開看不就知道了。”
提了提,似乎有墜重感。
她只好抽出側面固定的細枝,從裏拈出一只塑封袋。
“是你的沒錯吧。”
袋子裏是一枚四葉草耳環,跟她丢失的一模一樣。
柳芝娴覺得,在康昭眼裏,這不是普通的塑封袋,而是一只證物袋,保存着柳芝娴的“犯罪”證據。
不過,價值不菲的耳環失而複得,柳芝娴展顏而笑,連帶小粽子也變得可愛,恨不得能做成标本保留。
“是我的。還以為找不回,心疼死我了。”
她從手提包掏出另外一只,拉下擋板沖着鏡子戴回去。
左看右看,還是這副最心水。
康昭靜靜看了會,欠身從褲兜抽出什麽,又扔了過來。
“還你。”
兩張百元人民幣,那晚她特地回頭甩給他的。
紅彤彤的,跟綠色的小粽子天生絕配。
柳芝娴回味過來,“幹什麽,我不要。AA,男女公平。”
又來了。
那種危險而又具有壓迫性的笑容。
康昭說:“你怎麽确定我後來沒有找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