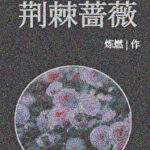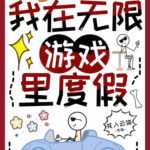5.判毋之章
在張家本家游蕩的張童啞并非無人管束。
當時族長把她安排給了族內的一位青年,那人叫張遠秋,對張童啞這位小輩算得上是關懷備加。他盡心盡力地把自己所學的一切教給人偶:教她識字,教她發丘指的使用方法;教她人最基本的情感(雖然沒學會),教她為人處世的道理。
張童啞對這位名義上的長兄也算得上是敬與謝。
族長對這個拼湊起來的家庭感到十分滿意,就連張海客也曾一度認為,這樣美好而又平靜的生活,張童啞會一直過下去——只要張家不出岔子,她就能扮演一位真正的人,由此活下去。
張童啞剛來張家的那段時間裏,她喜歡和張海客玩。兩個半大點的孩子天天掏蛋逗狗,惹得族裏的長輩頭痛不已:你說張海客是個混子吧,但人偶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是真正的快樂;你說張海客是個合格的朋友吧,這人又三天兩頭地惹哭張童啞。
“張海客,我要這個。”
人偶指了指在樹上露出半拉的老鷹風筝,面無表情地扭頭看着張海客。張海客聽了這話眼珠骨碌兒一轉,笑得像個狐貍:“這東西有什麽可玩的。”
“我想要玩。”
張童啞眼巴巴地盯着樹杈子,又扯了扯張海客的衣角,示意他幫忙。但張海客這時就像瞎了一樣,只是蹲下看着人偶,蠱惑般道:“你叫我一聲哥,我就給你拿。”
什麽鬼東西。
人偶在心裏默默吐槽,但又有求于人家,不敢表現在面子上。見張童啞半天沒動靜,張海客只好默默起身嘆口氣:“唉,昨日剛買的上好的糕點,本來打算和你放完風筝一起回去吃的……”
威逼利誘!
張童啞鄙夷地瞥了眼張海客,心覺這人是真不要臉。但她又特想玩這東西,也不能直接開吵。
想到這兒,人偶覺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癟癟嘴就要哭出來(其實她不知道什麽是哭,如何去哭,只是裝作委屈)。正巧,剛處理完政務的張遠秋打算出來散散步,就見倆孩子站在後院的那棵大樹旁不知在做些什麽。他眯眯眼剛想湊近瞧瞧,就見氣氛有點不對勁兒:那平日裏和張海客在一起最鬧騰的孩子現在咋一聲不吭的?
那一刻,張遠秋內心警鈴大作——
“張海客!你又欺負童啞!”
事情的最後以被訓斥了一頓依舊樂呵呵陪玩的張海客落幕。
當然,張童啞心裏的童年不止這些。
當張海客把另一個孩子領到這裏時,張遠秋就覺得自己的宅子是愈發危險了。
張童啞總喜歡盯着那孩子看。張海客問她是不是顏控,人偶只是冷淡地瞥了他一眼,又立刻恢複常态道:
“我覺得吧,他和我是一樣的。”
“你覺得你們哪裏是一樣的呢?”
“眼睛。”
人偶指了指自己的眸子,那如雪般灰燼的瞳孔惹得那孩子也為此感到驚詫:“你的眼睛。”
“是灰色的!族長說我的眼睛像長白山上的雪,因為我是從那裏來的,舍不得那邊的雪,就揀了兩片放在眼睛裏。”
那孩子思索了一陣兒,淡淡開口:“我們不一樣。”
聽了這話,張童啞急了:“我們哪裏不一樣啊?”
“……不一樣。”
張海客還沒來得及捂住他的嘴,話就脫口而出。見那人一個勁兒地反駁自己,人偶扁扁嘴委屈地跑進屋裏找張遠秋去了,留下張海客和那孩子在雪地裏幹瞪眼。
事後,張遠秋又教育了張海客一頓。
最讓張童啞感到幸運的一次經歷,莫過于年三十晚的那場大雪。
那年張海客沒回去過年,選擇留在本家陪張童啞和另一個孩子。于是等到過年的時候,倆人就手拉手跑到張遠秋的宅子前拜年:
“遠秋,新年快樂!祝你萬事順遂平安喜樂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前半句話聽起來還挺順人心意的,但越說越偏,聽得張遠秋差點沒忍住把這混子扔出去:“張家人天生長壽,別告訴我這一到冬天把你腦袋給凍壞了,本家可不負責賠償。”
正在院子裏玩雪的張童啞一個沒忍住笑了出來。這不笑還好,一笑張海客就盯上她了。
“喲!童啞在玩雪啊!來,讓哥和你一起玩!”
“不要。”
人偶緊緊地護住自己懷裏那堆了一半的雪人,警惕地盯着張海客。張遠秋見小孩這樣還以為自己是養了只随時随地都會炸毛的兔子。
“行了張海客,你什麽時候成她哥了。謀權篡位,該當何罪啊?”
站在張海客身邊一直沒出聲的孩子冷不丁冒出一句話:“扔下去喂粽子。”
此話一出,張遠秋也沒忍住笑了出來。張海客又氣又笑地看着那孩子,心裏也油然升起了一絲欣慰:這孩子終于肯開開玩笑說說話了,不然哪天自個兒悶死了都不知道。
年夜飯是張遠秋做的。
他包餃子有個習慣,喜歡包一個“銅板餡”的餃子藏在最底下,等飯端上來後再悄咪咪地夾給張童啞。盡管張海客已經不止一次問道那銅板的來歷,但張遠秋對此卻閉口不提。
不出意外,今年吃到“銅板餡”餃子的還是張童啞。但張海客和另一個孩子也吃到了隐藏餡餃子——裏面包了朵海棠花。
“快點過來!張——遠——秋——別忙公務了!”
張童啞左手牽着張海客,右手拉着另一個孩子,站在宅子門口沖裏面嚷嚷。批公文批到一半張遠秋無奈下樓,就見人偶只套了件麻布衫,像個傻子一樣站在雪裏。
“你在站下去非凍死不可。”
張遠秋把自己的圍巾給張童啞圍上,無奈道:“又想整什麽幺蛾子啊?”
“你過來就知道了。”
人偶拉着他們仨走,走進了一個大大的圈裏——
“你看!這是我用雪球圍成的一個大大的愛心!我把你們都放在我的心裏了!那你們在新的一年可不可以向我保證,不要離開我?”
從高空俯視來看,他們四個還真就站在一個大愛心裏。
人偶沒有心的。
于是在今年冬天,她親手用雪為自己堆砌了一顆愛心。
一顆能容納下她兩年內所有美好回憶的愛心。
一顆沒有留下遺憾的人偶之心。
但變故,總是來得比幸福快。
“張童啞!你在做什麽!”
那是一個永遠都不會平息的風雪夜。
剛和族裏另一位“自閉症患者”探讨過人生哲理的張海客領着那孩子走過張遠秋的宅子,卻見那屋內沒有像往常一樣亮着橘黃色的油燈,而是黑漆漆的一片,像被黑雲籠罩的雪山,惶惶不安。
“血腥味很重。”
站在張海客身旁的那人淡淡地抛出一句話,徑直朝院內走去。張海客本想說些什麽,但那孩子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既然他說不對勁,那大概率就是出事了。
“張童啞——”
張海客兩只手搭成一個喇叭放在嘴邊,大聲呼喚着人偶的名字,但這次回應他的沒有那道淡漠的目光,而是從屋內扔出的一盞煤油燈——
“砰——”
那煤油燈盞擲地有聲,等張海客回過神來再去看屋內的情況,裏面早已燃起了熊熊大火。肆虐的火舌舔舐着一切黑暗的傷口,仿佛一頭永遠不知疲憊的野獸,悄無聲息地摧毀着那近一年的溫存。張海客不知道屋內究竟發生了什麽,但最先闖進去的那個孩子已經在想辦法挽回損失了。
“張童啞——!”
張海客又喊了一聲。
這回扔出來的不是東西,而且也不是從窗戶裏扔出來的。這回被扔出來的是張遠秋,他滿身狼藉,全身上下都挂了彩,奄奄一息地躺在雪地裏瘋癫地笑。
“媽的張遠秋你笑個什麽啊,想吓死我?”
張海客略帶嫌棄地看了眼張遠秋,吐槽道:“你們兄妹倆鬧矛盾了?我見先前你倆關系還不錯。張童啞那孩子除了沒共情能力,其他的都很優秀。”
“呵……張家……”
張遠秋的話還沒說完,就被從暗處竄出來的黑影狠狠踹了一腳。那速度之快都現出了殘影,讓張海客一行人心裏咯噔了一下。
“張童啞,你就是一個人偶,就是一個工具。張家遲早要玩,你活不長久。”
此話一出,張童啞提着燈盞的手滞了滞。她那個時候應該是在思索,思索“工具”這個詞的意思。但張海客明白,張遠秋這話但凡被張家任何一個人聽到,活剮了都不為過。更別提是落在這個人偶的手裏——她沒有任何的共情能力。
果不其然——下一秒,張童啞的神色突然冷了下去,全然沒有了平日裏那副較好相處的模樣。那只提着燈盞的手毫不留情地砸了下去,重重地砸在了張遠秋的身上。
“我不會讓你死,張遠秋。”
“你教過我情感的意義,所以我不會在這裏解決張家的事情。”
罕見的,張海客竟從人偶的話中讀出了幾分悲涼:“我會将今日之事全盤托出,張遠秋,我們兩清了。”
說完這句話,人偶轉身離去。她走得匆忙,一片雪塵與火光都不曾帶走。張遠秋還趴在雪地裏大口地喘息着,咳嗽着,仿佛要把自己的內髒都咳出來。那個被張海客帶過來的孩子同樣神情淡漠地見證着一切,一聲不吭,像一尊雕像。
張海客遲疑了兩秒,給躺在地上的人扔去了一塊布:“擦擦你的血,我嫌髒。”
張遠秋無聲地搖搖頭,沒再說話。
良久,那位站在早已被燒得破敗的房前的男孩才開口,淡淡道:
“張海客。”
“嗯?”
“她是人偶。”
“嗯。”
“你剛才從她身上感受到了悲傷的氣息,對嗎?”
那一刻的人偶是懊悔與悲涼的。
後來張海客在那處被燒得只剩下和灰燼的房子裏找到了把自己縮成一團的張童啞。
人偶的身上冰冷無比,張海客帶來的那盞煤油燈不能暖熱她冰冷的胸腔。
張海客慢慢蹲下去,擁住了人偶,把她的腦袋靠在自己頸窩上。出乎意料的是,張海客感到了幾滴冰冷的液體緩緩滴落在自己的皮膚上。
“童啞?”
張海客小心翼翼地呼喚她。
“嗯。”
人偶悶聲回了嘴。
“別哭了,好嗎?”
那是身為人偶的張童啞第一次品嘗到“悲”的滋味。那感覺十分苦澀,像之前自己不小心吃到的一瓣酸橘子。
她從張海客的懷抱中離開,随意抹了把臉:那從自己眼角淌出來的液體冰涼,卻又充實着溫熱。這和長白山上化了的的雪不一樣,這是一種多情的雪。
想到這兒人偶又重新窩回了張海客的懷裏,緊緊抓着他胸前的衣襟,小聲啜泣了起來。
哭,并不是一種好的滋味。
張遠秋是叛徒,但也教會了張童啞人擁有情感的意義。
只可惜他不是一位稱職的老師——因為人偶啊,她在後來的歲月中,再也沒能領悟其本身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