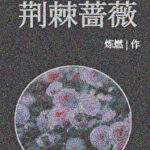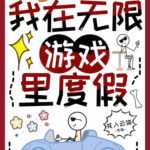“徐少微!你居然還真逃回來了!”
均平府前,阮氏骨血終于現身,衆人的眼神無不彙聚了過去,似乎不論修為深淺,都想要看穿她面部那道白光,唯有太史宜,他精通天魔無相感應法,只是掃了那阮氏女兒一眼,便不屑地哼了一聲,轉向陳均背後的徐少微,喝道,“你這般女子,毫無家教,不知廉恥,做下的事情連我都羞于啓齒,若是張揚出來,只怕連上清門的臉面都要跌盡了!我今天就要代你家人好生教訓教訓你。”
他這話大有文章,那些看不穿遮面白光的修士,不禁都聽得興奮起來,似乎很盼望太史宜叫破了徐少微做下的醜事——這兩個修士在南株洲相争,一路跌落幽冥瘴澤,孤男寡女,能發生什麽事,叫太史宜一個元嬰修士氣成這樣?
徐少微跪坐在陳均背後,舉袖遮面,叫人看不清神态,陳均卻很從容,和聲道,“太史道友又何必動氣?你也代不了少微家人——有些事,不妨回了中央洲,再到我上清門來和她家裏人當面說道,少微不懂事,你和她計較什麽?”
衆人不禁交頭接耳,卻是泰半修士都不明白這其中的典故,只有道宮中幾位執事低聲道,“陳真人所言有理,太史令主這話說得過了,徐仙子家中自有洞天長輩,也輪不到他為徐家做主。”
“徐仙子家中的洞天長輩,可是上清純陽演正天徐老祖?”
“正是,若不是徐老祖的名頭,太史令主怎能讓她從幽冥瘴澤毫發無損地逃回來?說是不好以大欺小,但魔門修士,動了真火還管這許多?太史令主別看面上粗豪,心中卻是有數,讓陳真人出來,無非柿子撿軟的捏罷了,陳真人背後大概無人支持,又和他一樣是元嬰修士,只能在他身上找個場子了。”
他們在道宮中低聲議論,太史宜卻仿佛聽見了似的,沖着壇城方向冷笑三聲,宮主心中大駭,忙祭出一盞青燈,将煙氣也順着那笑聲吹了回去,又以秘法傳音,嚴禁壇城議論天魔令主,“你們不要命了?南株洲魔門式微,你等是真不知魔修的厲害,天魔無相感應法修到深處,便是相隔千萬裏也可以呼名感應,更別說如今這麽近的距離,便是要說,也說些他的好話!”
道宮中,那幾個金丹期執事先聞得笑聲,只覺得心旌動搖,胸中煩惡,竟是不知不覺間道基都被沾染,好在随後青煙飄入,解開魔法,這才知道厲害,連忙謝過宮主,卻是再也不敢多嘴。只聽太史宜對陳均道,“不錯,徐少微不懂事,我只找你算賬,她做了什麽你很清楚,陳均,你說,你們上清門就是這樣管教弟子的?”
陳均嘆道,“少微這番的确是做錯了事,也觸犯了門規,我們上清門處事一向公道,錯了便是錯了,太史道友也不必如此誇大其詞,少微一個人的事,怎麽和我們上清門的聲譽就扯在一起了?”
“好!你既然知道她做錯了,那該如何給我一個交代?”太史宜捉住陳均這個話縫窮追猛打,陳均雖然已經出面,但魔雲之中,天魔令振動的頻率卻是越來越高,惹得魔雲陣陣激蕩,若不是均平府中散發出一股鎮定平息之力相抗,只怕此時壇城上方的空間,已經開始不穩了。
歸一門、寶芝行兩大修士虎視眈眈,還有諸多茂宗修士暗中窺伺——雖然是茂宗出身,但只是宗門力量無法和盛宗相抗,修士的修為,未必就弱了多少,這許多元嬰修士的關注,只在均平府前的一人。陳均卻是夷然不懼,微微一笑,說道,“這不也簡單嗎?我上清門從不包庇弟子,若是少微無錯,太史令主的法藏令,今日也少不得要領略一番了。”
他話中信心十足,似乎對這法藏令極是期待,并不畏懼,衆修士都不禁暗自皺眉——風波平磬只能鎮定法藏令,但現在無極神光和寶芝金錢都已露面,陳均底氣還這麽足,莫不是除了風波平磬和一氣雲帆之外,還帶來了別的洞天靈寶?
陳均自然不會解釋,頓了一頓,又笑道,“但少微既然做錯了事,那我們上清門也絕不會護短,今日便把她交給太史令主懲戒,要殺要剮,随令主發落。”
他将袖子一拂,徐少微身上頓時現出一道道繩索,将她雙手縛住,送往太史宜方向。太史宜也為之一怔,不及多想,見遮護徐少微的法力單薄,如今衆修環伺,若是被人劫走,徐少微法力被封也無法反抗,便先發起一道黑光,将她攝到面前,驗看過确是徐少微無誤,這才狐疑道,“你什麽意思,要殺要剮——我若真殺了她,你也就這麽看着?”
陳均見他嘴上喊得兇,接人倒快,不由微微一笑,從腰間摘下一柄折扇,在膝上一格格張開,“少微做的錯事,令主心中最是有數,令主覺得怎麽罰公道,就怎麽罰,令主覺得殺了她公道,那便殺了她好了,少微既然招惹了令主,自然也該承擔後果,上清門只是少微的師門,又怎能不分是非,一律袒護到底?”
如上清門這樣傳承遠古的盛宗高門,門中峰頭林立,各系勢力錯綜複雜,的确要有嚴明門規,方能統合各方勢力,衆人都不由暗自點頭,覺得陳均處理得甚是妥當,宮主心中更是暗道,“不愧是盛宗二弟子,陳真人好會說話,師門不能不分是非,一律袒護——只有親人才能這般,他這是告訴太史宜,若真是以大欺小,殺了徐少微,回到中央洲,純陽徐真人也自會找他尋仇算賬。”
陳均話中真意,并不隐晦,只要知道徐少微身世的修士,多數都能明白過來,太史宜雖然煞性大發,但如他這般的元嬰修士,永遠不會完全迷失心智,垂首望着跪坐在腳下的徐少微,悲面、怒面轉來轉去,片晌後哼了一聲,對徐少微道,“你的替命金鈴呢?交出來。”
徐少微一反平時那顧盼自得的樣子,雙眸含淚,楚楚可憐,微微舉起右手,欺霜賽雪的手腕上正籠着一串金鈴,太史宜為她解下,捏在手中,道,“金鈴在手,我已取走你一命,但今日之事還是不能就此算了,我說過,你不懂事,家裏人不教你,我來教你。”
說着,将徐少微淩空舉起,伏到自己膝上,手掌凝起黑氣,打在徐少微臀上,喝道,“此後可懂事了?”
衆人都是目瞪口呆,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反應才好,便是陳均臉色也有些微妙,似是想笑又不好笑,他咳嗽一聲,舉起折扇遮面,偏過頭去,道,“這可看不得。”
“不錯。”宮主心中一凜,也是忙傳音回去,壇城前方頓時凝起濃霧,便是諸多盛宗洞府,也紛紛張開濃霧遮護——太史宜可以當衆懲戒徐少微出氣,上清門有話在先,也不會幹涉,但這熱鬧卻不是好瞧的,身後沒有洞天真人遮護,最好留個心眼,上清門的金丹真人,竟被燕山令主在大庭廣衆之下,如此折辱,将來徐家長輩要維護徐少微的清譽,誰知道會不會一句話就取走當日所有低階修士的性命?
便是會仙子和諸掌櫃,也是啞然失笑,收了神通轉身沒入洞府,不願結這個因果——縱使在洞府中也能感應到外面的景象,但不是親眼目睹,多少留了個退步。壇城前濃霧四起,魔雲漸漸散去,太史宜打了徐少微幾十下,徐少微忍不住喊了起來,叫道,“好痛,好痛!”
若是尋常掌擊,便是千下萬下,她一個金丹修士也不會當回事情,太史宜掌中含了法力,徐少微又不能調用靈力相抗,自然痛楚不堪,太史宜聽她語調中已有哭音,最後拍了一下,将她松開,喝道,“以後還敢麽?”
徐少微垂頭嗚咽道,“我知錯了。”
她雙手被縛,又無法力,歪倒在太史宜腳邊,看着極是可憐,太史宜哼了一聲,伸手一指,她周身仙繩化作片片飛灰,三頭六臂也收了起來,仍是那長眉入鬓的年輕武将模樣,遙遙将陳均看了一眼,道了聲,“好個陳老二,小瞧你了,可惜,你用了這麽多心思,還是找回個西貝貨。”
說着,回身一步邁入虛空,消失不見。
徐少微見他走了,舉袖掩面,回身飛到陳均身邊,遁光緩慢搖晃,顯然太史宜給她留的傷不輕,到了陳均身邊,她放下袖子,擡起頭來,面上卻是幹幹淨淨,毫無淚痕,雙目黑白分明,哪裏是哭過的樣子?
陳均看了她一眼,嘆道,“少微,你也多少顧忌些顏面罷。”
徐少微坦然笑道,“二師兄,我不要臉,我要突破元嬰。這次我知錯了,下次還敢。”
陳均無言以對,搖頭嘆息,伸手一卷,将徐少微和阮氏女裹起,轉身要投入均平府時,只聽身後有人道了一聲‘且慢’,他回過身去,微微一怔,眯起眼望着天邊極遠處那白玉車駕,低喃道,“越公子……”
壇城前,道宮宮主才放下的心又提了起來——看來,今日的紛争還沒有結束。
“他們為什麽都走了?”
均平府內,松軒左近,少年少女并坐在一個塌了半邊的小亭之中,一同看着瞿昙越手裏捧的銅鏡,鏡中将府外情形一一映出,府外人似乎就連太史宜都一無所覺,阮慈問道,“是不是已經看到了容姐,便知道了她其實不是真正的劍使?”
“不錯,娘子果然聰慧。”
瞿昙越還是那笑眯眯的樣子,“容姐已拜入上清門,習了上清門的開脈法訣,若她是東華劍使,開脈之後當可和東華劍建立聯系,會真人和諸真人都曾見過謝姐姐運使東華劍的樣子,對東華劍存有感應,只要見到了容姐,他們便知道上清門這一次算是栽了,費了那樣大的力氣在魯國搶回了阮氏骨血,卻不料也是個假貨,身上根本沒有東華劍。”
他口中稱謂,都是跟着阮慈叫的,阮慈其實覺得有些奇怪,但也沒有糾正瞿昙越,只道,“你也見過謝姐姐用東華劍麽?”
瞿昙越笑道,“這是自然,謝姐姐殺了我好幾個兄弟,我還要多謝她呢,若不是她,這少門主怎麽輪得到我來做?”
阮慈心想,“看來玄魄門中,争鬥也很激烈。瞿昙越若是能把我帶回到玄魄門,地位應當能更穩固幾分。”
她如今已知道為什麽陳均不放她出去走動,也知道老丈為什麽要給她那枚天命雲子,想向瞿昙越打聽一下,上清門中是否有這麽一個愛下棋的老丈,話到嘴邊又縮了回去,只道,“難怪陳均帶了容姐出去,便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太史令主打了幾下徐真人的屁股……要走了那個替命金鈴,便雷聲大雨點小地走了。”
瞿昙越冷笑道,“太史宜和徐少微這是說好了罷,一唱一和,迫陳均把人交出來。看過的确不是劍使,好戲可不就該收場了?太史宜把替命金鈴拿走,徐少微難道不能找他要回來?這替命金鈴其上自有禁制,他拿走了又有什麽用。”
又道,“陳均的心倒還算是正的,可惜孤掌難鳴,還得等徐少微在幽冥瘴澤鬧出點事情了,才把你收到均平府裏藏起來。”
他這話都是自己的推測,但聽着卻句句入耳,上清門中勾心鬥角、暗潮洶湧的态勢,竟被這番話描摹出了一多半來,阮慈沒有接話,默默地坐着,瞿昙越又笑了起來,溫柔地說,“你實在不願意離開上清門,随我到玄魄門去,那我也沒法,只是以後若有事用得着,你記得找我。”
阮慈點了點頭,見瞿昙越起身欲走,不由又叫道,“官人……”
瞿昙越止住腳步,含笑問道,“怎麽了麽?”
阮慈欲言又止,終是說道,“能不能請托你一件事?”
瞿昙越不由笑了,“你有事不和我說,該和誰說呢?”
他這話說得,仿佛真和阮慈心意相通一般,其實兩人并肩而坐,阮慈哪有一刻放松了警惕?只是這件事她實在忍不住。
“你這番為了找我,一定命令秀奴和麗奴找了不少宿主罷?”
她有些吞吐,低聲說,“我知道這些宿主對你們來說,未必只有尋我一個用處,不過……不過,現在已經知道我在這裏了,能不能讓它們別再寄宿南株洲的百姓了。”
此事以兩人實在交情來說,實屬非分,但确實是阮慈一塊心病,她嘆了口氣,禁不住道,“百姓們真的好可憐,為了一柄東華劍,受了多少牽連,少一分折騰便是一分罷。”
瞿昙越沒想到阮慈如此慎重其事,說的竟是這話,不由也怔了一怔,望向阮慈的眼神,似乎比從前多了一絲不同,他笑着道,“我若是答應你這件事,你又該怎麽賠我呢?”
阮慈心想,我現在能辦成什麽?你無非要我一個許諾。
這件事她牽挂已久,只是從前不見瞿昙越,也無從談起,現下即使知道瞿昙越要她辦的事也許棘手刁鑽之極,卻仍然毫不猶豫,慨然道,“你要我辦什麽,說來便是。”
瞿昙越深深看了她一會,突地笑彎了眼,伸手折下亭邊一朵雙色寒萼,插在阮慈鬓邊,又為她微微挽了挽鬓邊散發——剛才連番大震,阮慈的發髻也有些松了。
“騙你的,不過小事而已,”他說道,“南株洲能有什麽布置,比讨娘子的歡心更重要呢?娘子收我一朵鬓花,也就夠了。”
阮慈不料他答應得這般爽快,不由歡喜無限,撫了撫寒梅,沖他粲然一笑,心甘情願地叫了聲‘官人’,“多謝官人疼我。”
瞿昙越懷中圓鏡,依舊映照着府外的情狀,白雲茫茫之中,各家元嬰修士遙遙對峙,一副大戰一觸即發的樣子,但均平府內,殘垣斷壁之中,少年少女卻是相視而笑,說不出的旖旎風流。
阮慈年少初成,平日裏不見傾城傾國,只這一笑燦若春華,瞿昙越眸中不禁浮現一絲驚豔,近前一步,在她耳邊輕聲說道,“其實,太史宜和徐少微在幽冥瘴澤的确起了些不該起的沖突,我費了好大的功夫,壞了徐少微進階元嬰的好事,但這些龃龉,也遠遠沒到他們表現出來的地步。”
“徐少微和謝燕還素來親厚,我是為了你着想,也是為了找個機會,進均平府來找你——你在上清門裏,一定要處處小心。可要知道,修士壽歷千百,沒有哪個大修士是太太平平修到如今的,有些人的心機,遠超你現下的想象。”
他對阮慈眨眨眼,笑着說,“你看,我不就很會騙人嗎?”
他的身形緩緩消散,阮慈在亭邊坐了許久也沒有動彈,依舊望着瞿昙越遠去的背影,過了一會,她回頭說道,“盼盼,你既然來了,就出來罷。”
一只橘色小貓從林間緩緩踱出來,王盼盼沖遠處瞿昙越的方向嗅了幾下,說,“越公子好會呀。”
阮慈道,“會什麽?”
她站起身和王盼盼一起回去,王盼盼跳到她肩頭,偏頭說,“他挺歡喜你的,你不覺得嗎?”
“那我情願他只是想要我和他一起去玄魄門。”阮慈說,“他都幾千歲了,我才十幾歲,他歡喜我?他不歡喜我也還罷了,若是真歡喜我,那才惡心呢。”
王盼盼嗔道,“你這個人!哪有這樣說的!真是不解風情!”
阮慈笑道,“我這個官人若有孩子,我現在大概和他玄玄玄玄孫子一般大。他歡喜我?若不是他這個化身只得煉氣期修為,我怕他一拳把我打暈了帶走。”
一人一貓争執不休,回到小慧風,王盼盼也從阮慈口中聽到了瞿昙越的說話,它在床上滾來滾去,不快地道,“我說徐少微雖然頑皮,但一向還算罩得住,怎麽突然捅出這麽大的漏子,搞得自己顏面掃地,原來有他在其中弄鬼,我本來睡得好好的,突然被震到地上,這筆賬我記到越公子頭上了。”
阮慈坐在桌邊,不禁攬鏡自照,摸了摸鬓邊的梅花,王盼盼躺在床上舔了舔爪子,又道,“不過這樣也好,太史宜看到了阮氏骨血,陳均也借他之手,讓衆人都看過你那個姐姐。既然劍使不在上清門手裏,接下來直到回到中央洲,均平府應該都會平安無事,你也總算可以拜師修道,開脈煉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