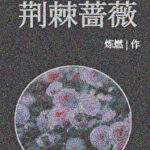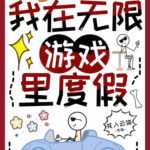天下豈有無道之處乎?三千大道,遍布虛空宇宙萬事萬物之中,道韻之争,永遠沒有止息,虛空宇宙也就永遠都沒有無道不法之地,此時琅嬛周天之中,交通大道、時間大道轉為低弱,自有大道應運而起,占據他們在氣勢場中留下的空缺。倘若完全無有大道填滿,那麽便會有虛數力量滲透,譬如天魔,便是這般侵入諸多無主大天,引來浩劫。
此時琅嬛周天之中,因涅盤道祖內景天地之中,玉池與湖心島都已恢複舊觀,道基也重新煥發生機,雖然在回歸靈脈之時,被兩大道祖聯手攔阻,但涅盤大道亦是蓬勃奮發而起,占去了許多空餘,阮慈的太初大道,也毫不客氣地将剩餘的空地搶占,至此在琅嬛周天之中,終于有了一席之地,可以和其餘道祖真正博弈。而此時琅嬛修士紛紛感應機緣、踏破瓶頸,其實亦是洲陸合一,大道變動的體現。洞陽、太一二人的傳承在琅嬛周天內都并不顯赫,此前雖占據大勢,但并無弟子可以應運晉升,而此時涅盤大道上揚之後,周天之中鳳凰遺族均得恩澤,還有許多元嬰修士,修持的都是那等被這兩大道韻壓制的大道,如今自然也有一奮起之勢,迎來了自己的機緣。
阮慈在恒澤靈山之巅盤膝而坐,此時對周天大勢,已是了如指掌,知曉了其中深處的道理,舉目望去,見上清門處氣勢沖霄,也不免微微點頭一笑。上清門王謝二家,均是舊日宇宙傳承而來的鳳凰遺族血脈,此次自然得到不少好處。再有太微門、青靈門等,也都分潤到了不少沖天之勢,究竟琅嬛周天亘古以來,便是桀骜不馴,便是洞陽道祖占據了周天,因大道本質之故,他既然封閉了本方周天,那麽寶芝行這樣以經商為主的門派,便很難發展起來,畢竟無有和外界的交流,商行勢力終是有其極限,各家宗門,并未受到太多打壓,因此方才有了如今周天之中,百家争鳴,處處開花結果的盛況。
此局告一段落,琅嬛周天往大玉周天發去的那淩厲一箭會造成怎樣的結果,還要到天外觀照,才能知道詳情,但阮慈如今可是不敢踏出天外一步,便連化身都不肯放出,畢竟周天之外,還是洞陽道域,自己這一招算計了太一君主,倒也罷了,其在洞陽道域中已無餘力,但得罪了洞陽道祖,可不是鬧着玩的。雖然如今看來,是自己和涅盤道祖得了最大的好處,但這種局勢,危若累卵,随時可能翻覆,到時阮慈要承受的報複有多猛烈,便要看洞陽道祖的心胸了。
她甫一回歸,成就洞天之餘,便又迎來了這連番變故,直到此刻,方才漸得安寧,心下也覺有些疲累,見四方風起雲湧,諸般洞天都在看顧洲陸弟子,只有王真人站在遠處等候,卻依舊是真身在此,便對他伸出手去,王真人微微搖頭,卻仍是現身在她身側,伸手要将阮慈拉起身來,卻被她拉在身側,二人并坐着靈山巅峰,阮慈問道,“你這遺族怎麽沒收到什麽好處?”
王真人淡然道,“洞天真人,早已洗練骨血,唯有存身之道,法體越是無關緊要,便也越難分潤血脈而來的好處。”
這其實也并非什麽壞事,洞天真人,修為越高,距離合道也就越是接近,若是突飛猛進,很可能要被迫合道,對大多數洞天來說,這都相當于迎來自身的隕落。王真人合道的機緣,應當在琅嬛周天這一次大劫之後了,阮慈點頭道,“我們紫虛天一脈,所得最多的應當便是鳳羽。她收了鳳阜河中的鳳凰遺血,借此煉就元嬰,和遺族的關系也最緊密,只是……”
她未能說完,心頭亦有少許愧疚,王真人心領神會,低聲道,“你是擔心那随了乘雲子而來的人麽?”
那黃衣修士道號正是乘雲子,其在琅嬛周天內游歷時,都是在各處挂過號的,而天外修士的來去,也瞞不過瞿昙越的神念,乘雲子去而複返,不免引來他的注意,當時琅嬛洞天,神念都和靈雲鏈接,只需要一個念頭,莫神愛便自然飛入甬道,借機往外觀照。阮慈也分出一縷心思,仔細看了乘雲子幾眼。
乘雲子真身雖然清清白白,但虛數中各個維度,卻多有可以憑借之處,他自己是懵然無知,沒有什麽線索,莫神愛也沒看出所以然來,阮慈卻是隐約有些因果感應,猜到涅盤道祖感應到自身道基複原的機緣已至,便在虛數中借機依憑,回返琅嬛。但此時琅嬛虛數之中,風暴方興未艾,由黃掌櫃和闵、華二人掀起的風波,還遠遠未到停歇之時,甚至可能會席卷宇宙虛數,虛數不好落腳,更難入內,或者便會憑借如今這興盛之機,在這些修士溝通大道,晉升之時,在實數之中為自己找個宿主寄身。
若是如此,最好的人選自然是阮慈,不過對阮慈出手,無異于挑起大戰,連白劍尚且不敢同時杠上幾名道祖,更別說還在虛數之中的涅盤了。退而求其次,傳承了鳳凰血脈的秦鳳羽,或者便會是涅盤道祖的選擇,而阮慈也不便出手,一來這是秦鳳羽自身道途,危險和機遇一體兩面,阮慈若是插手,或可保得秦鳳羽性命,但她在大道上将不會再有絲毫進步,二來阮慈自己多番借光,欠下涅盤道祖不小人情,重煉道基,也只是為了限制洞陽和太一在琅嬛周天的權柄,可謂是将涅盤道祖利用到了極致,此時也實在不好再去奪她的立足地。因此雖然心下不快,卻也不好出手,只能略對王真人傾吐一二。被王真人道破心思,也不答話,側身抱着他,将面孔邁入衣衫之中,只不說話。
王真人略略撫過她的肩背,道,“已是洞天高修,未來道祖,卻還如此孩氣。”
又道,“你也多慮了,一來道途波瀾,只在自身執掌之中,鳳羽若不願應對這般情形,當日便合該隕落在鳳阜河中。天地逆旅,個人有個人的始終,身為師長,哪能肩負所有人的道途,有時全其所求,比延其性命,更見恩義。”
見阮慈依舊不肯擡頭,又道,“再者你的性子,她也很是清楚,哪怕是防你記恨,必然也會留有餘地,多半是不會取了鳳羽性命的。”
阮慈明知王真人第一句話說得也對,但仍是聽了第二句方才開顏,擡頭喜滋滋笑道,“是了,說不準這對鳳羽來說,還是天大的機緣呢!”
見王真人凝望着她,但笑不語,便扯着王真人的袖子,連珠炮似的嚷着問道,“對不對嘛,對不對嘛,快說,對不對嘛!”
王真人吃不住鬧,搖頭道,“你說得自然都對!”
他明明說的是反話,阮慈卻也當做是好話來聽了,笑眯眯地舉起雙手,笑道,“我心裏疲累得很,一步也不願走了,我要你抱我。”
王真人對她,素來是沒什麽好話,行動卻依縱得很,起身先飛了一段路,看似不搭理阮慈,不知怎麽,阮慈身邊靈炁暗湧,又将她擁了起來,簇往王真人身側,阮慈偏不肯和他牽手而行,半途改了方向,躍往王真人背上,王真人便也由得她了。
阮慈這話,倒也并不虛假,自她被帶到青華萬物天,便幾乎是無窮無盡的波瀾起伏,太多大事,太多綢缪,幾乎令她靈臺生塵,此時雖然立起涅盤道基,暫得少許自由,但也知道諸位道祖絕不會善罷甘休,更何況周天仍在局中,一切遠未解脫,更大的風波還在後頭。唯有在王真人背上,受着他縱寵,方才得到一絲少女般的歡欣,心下歡喜寧靜,側首歇息了半日,方才柔聲問道,“恩師,你說我的洞天,起個什麽名兒好呢?和周天的連接點,便選在紫虛天一側,你說好麽?”
王真人微微失笑,卻也不急着施展空間神通,回返山門,而是負着阮慈,拔空而起,在那道韻亂流中緩緩前行,輕聲細語,和她一路商議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