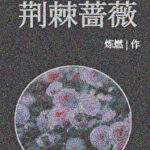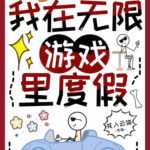“那就是劍使遁光嗎!”
“應當是吧,兩日前落入長耀寶光天的遁光便正是這個顏色,秋真人真是好體面,劍使從紫虛天閉關出來,往七星小築拜見過掌門,第二個便到了長耀寶光天來見秋真人呢!”
“聽聞邵真人也有意與劍使一晤,領略一番東華劍的風采。”
長耀寶光天位于紫精山要沖,周圍環繞十數峰頭,俱是門內要緊所在,亦有不少美姬力士來往其中,這數日衆人都是興奮不已,指點着長耀寶光天隐約可見的入口,此時見到一點明滅不定的白色遁光從長耀寶光天飛出,掠過天際,飛往紫虛天方向,幾個小弟子頓時叽叽喳喳,互相議論了起來。“真不知劍使大人是如何的威風,聽說三百年前在中央洲陸邊界,她一劍便削弱了燕山三成氣運,令到這三百年來,燕山弟子絕跡中央洲呢!”
“誰說的?上回連師兄來交差,還說起在翼雲渡口仿佛見到了燕山弟子蹤跡,又查獲到一批仙畫,似有魔氣蘊藏其中。”
“喂,你們可知現在洲陸中部的空間裂縫到底如何了?我下個月便要出門辦差,可門內地圖都還是百年前的玉簡,竟不能将這百年間的變動逐一載明,如今無垢宗和太微門越鬥越兇,小雷音山脈周圍傳聞已經是不能過人了。若是要繞路,又不知該怎麽走才太平。”
“你還是要去左近幾處坊市,尋寶芝行的貨郎買路,倘能和他們一道同行,便不太會出差錯了。”
三百年來,洲陸形勢幾番變換,如今又是一批新弟子嶄露頭角,自阮慈入道以來,所結識的同輩弟子,若是還未結丹,道途便也差不多沒什麽指望,再加上門內門外諸事頗多,未能突破,便是沉淪下僚,在一次又一次的任務中隕落。如今自南株洲而來的衆弟子中,便只有阮容、林娴恩二人猶存而已。便是她在九國內的下屬,栗姬等人也都先後絕了結丹之念,如今只一味經營望月城勢力,每過十年,便會将城中可堪造就的子弟送到捉月崖,由王盼盼挑選一番,若是有看得上禀賦的,便留在捉月崖執役數十年,也多少沾染些好處,便是未被看中,至少也能領略一番仙家風光,開闊眼界,也知道将來該向往仙途,而非是一意在九國中做文章。
至于遲芃芃、莫神愛等人,也都先後結丹,阮慈出關之後,少不得和各方好友傳信問候,她成功拔劍,門內門外都有賀禮送到,便連時間靈物,蘇景行也送了一味過來,純陽演正天亦遣人來賠禮道歉,言道良國之事,乃是其失察之過,聽聞劍使有意收集時間靈物,純陽演正天中那株仙藤,數千年內便會結果,便以此果作為賠禮雲雲。
在阮慈而言,能讓純陽演正天痛徹心扉的報複,自然便是殺死徐少微,讓徐真人的盤算完全落空,但此事沒有王真人支持難以辦到,徐少微深藏純陽演正天中,阮慈能耐再大,也無法攻伐洞天。此仇她也不願由王真人出頭,只是将純陽演正天賀禮并來人一道掃地出門,以示後日尋仇決心。王真人對此也無一語置喙,便仿佛是不知道一般。
她此番閉關出來,也有許多疑問,在天錄閣翻閱典籍未能得到解答,前往幾處親近長輩洞天拜會,也少不得坐而論道,将自己在道途中的種種玄妙體會向掌門與秋真人演示,這般論道,不止言語,極難描述,更像是道韻之間的碰撞與交流,玄之又玄,雙方各得些許感悟,阮慈只覺得有些疑問仿似已得到解答,只是那答案依舊藏在心中,還要自己尋找。而又産生了不少新的疑問——只覺得在道途上邁得越遠,也就越發能感到自己的無知,若不是門外兵兇戰危,更有那風波重重,洶湧澎湃,只等她際遇風雲,攫取氣運因果,真想在山中談玄論道,盡享那仙家逍遙歲月。
此次從長耀寶光天出來,便是與秋真人一脈相談甚歡,陳均這三百年來積累戰功無數,此時也即将卸任十大弟子,閉關沖擊元嬰後期,而周晏清成就元嬰不過是數百年時光,還在元嬰初期,正需要巨量資源,也是摩拳擦掌,欲要沖一沖那十大弟子之位。他有意和阮慈結盟,衆人把酒言歡時,便邀她道,“愚兄來日便要領命征伐魔門,劍使可欲與我同行?你身系周天氣運,這一去必定是風起雲湧,倘若能活着回來,此行氣運,必定不小,十大弟子之位,也就十拿九穩了。”
原來上清門十大弟子,并非是單看厮殺之能,除了要看師長地位、人脈乃至氣運之外,還要看每位弟子能攪動多少風雲,牽動多少氣運。按阮慈理解,氣運便是所有變化的總和,她去阿育王境之後,阿育王境便因她身上的東華劍而崩塌不存,因此在她活着離開阿育王境的那一刻,整座洞天殘餘氣運,自然而然便被她收攏其中。
十大弟子,無不是曾為上清門立下汗馬功勞,便是因此,他們的行為影響到了宗門将來的變化,便能收獲一份氣運,如陳均、徐少微、周晏清,都為劍使回歸門內出力,那麽上清門因阮慈而發生的許多變化中,他們便可收攏到一份氣運。而邵定星能坐鎮中軍,指揮大軍和燕山對峙,拖住了燕山中魔主所轄勢力數十年,這其中也有一份驚人氣運,被他占去了一大部分。
以此而言,阮慈身為東華劍使,十大弟子之位便不可能少了她的,她若有意首席,邵定星退位讓賢乃是勢在必行,但上清門大弟子也有許多繁巨事務,或許耽誤修行,阮慈亦未必耐煩。她若不願做,自可扶上一名羽翼,又或者便暫留邵定星幾年,待他辭任後,自己修為也臻入元嬰之後,再接過這個擔子,也不失為一個辦法。周晏清和阮慈商議的便是此事,不過說得并不很明白,若非王盼盼從旁指點,阮慈幾乎不明白他的意思。
“周師兄真是氣魄如虎。”阮慈也未曾想到周晏清初初晉入元嬰不久,便敢觊觎那個首席的位置,不免和王盼盼多說了幾句,王盼盼不屑道,“在我們琅嬛周天,能晉級元嬰的,哪個不是瘋子?”
阮慈想了一想,她認識的元嬰的确沒幾個簡單人物,仔細想來也就是呂黃寧和陳均似乎都是穩重性子,王盼盼對這兩個人名卻也嗤之以鼻,冷笑道,“陳均穩重麽?你那呂師兄若真穩重,徐少微怕他做什麽呢?她在門內最怕的便是這個呂師兄,說來你們師兄妹也甚是有緣,都對她有必殺之心,就不知道将來誰能踐諾了。”
阮慈奇道,“我修為雖比不上寧師兄,但怎麽說也有神劍随身,倘若真要争起來,難道還争不過呂師兄麽?”
王盼盼嘟囔道,“這種事也未必是只看修為的。”
此時遁光已到了捉月崖前,王盼盼從靈獸袋裏跳了出來,叫道,“喂!你下回有空,便把那傻鹿兒叫出來玩耍罷!”
這三百年來,王盼盼都在捉月崖藏身,除了主理內務之外,也頗是寂寞,便連那小熊英英,也是養在紫虛天內,阮慈笑道,“曉得了,只是他現在化形未久,膽魄仍弱,別說出紫虛天了,便連走出天錄閣都猶豫再三,你且耐心再等一段時日。”
王盼盼尾巴一甩,不屑道,“若是按你所說,這化身只怕數千年內都難以催化,也不知是誰用大法力溫養灌注,才将那小鹿兒在三百年內又催生出來,既有這般能為,你便再求他幾句,說不定傻鹿便又可化為人形了呢?”
它對王真人素來十分避諱,也難得如此直白地影射,阮慈聞言,笑容不由微收,片刻後小嘴一嘟,淡淡道,“算了,還是順其自然好些,求也求不來,誰知他又有什麽用意了。”
提到王真人,也不願叫恩師,以‘他’為名,心中似仍存了些怨怼,卻也不知還在怨些什麽,王真人對她,可說是用心良苦、無微不至,阮慈按說不該有氣,可提起他心中又有些不得勁兒,出關之後,又怕真人召見,可真人對她不聞不問,她又漸漸更為不快。
送走王盼盼,回山路上,不由将那九霄同心佩又掏出把玩,她尚且還未煉化,只覺得此佩隐隐也有一絲抗拒,畢竟此前被無情抛棄,玉佩尚未有成形器靈,但也隐隐覺着委屈。
如今真相水落石出,阮慈心中對這玉佩也有一絲歉疚,幾番把玩,更是聞言說了不少好話,她倘若将這些好話中哪怕一句說給王真人聽,師徒之間似乎也不至于繼續尴尬下去,只是阮慈卻偏偏不願,出關數月,也就是今日回山,念及還有許多疑問想和王真人談論,這才飛往那海邊小院。見院門虛掩,嘴角也是微翹,便推門而入,也不看王真人,低頭行禮道,“徒兒拜見真人。”
這六個字冷冰冰的,也不肯表述什麽思念之情,榻前那化身‘呵’地笑了一聲,卻也未有動怒,淡然道,“終于來了。”
不論阮慈如何,王真人待她總是這般,他對阮慈的好,總在阮慈所不見之處,便是她性子刁鑽,身受深恩,不思感激,反而還要加倍刁蠻,他也只是這般淡然。阮慈瞟了他一眼,見王真人色秀如竹,趺坐在白玉榻上,心中不知為何,突然想道,“倘若我打他,他躲得開嗎?”
這化身不過也就是金丹中期修為,阮慈有東華劍在,已不能簡單以境界來衡量戰力,不過此處是紫虛天,乃是王真人內景天地所化,王真人化身在此處應當是無人可以匹敵。便連阮慈,要拿下她也不過是一念之間。她的荒唐心思,終究是不可能成真了。
再看王真人,對自己這悖逆之想似乎毫無所覺,也不見用茶,也是暗自點頭,“看來如今他也終于看不穿我的心念了,這是好事,此時洞陽道祖應當也不能再查閱我的思緒,便是和我有關的人事物,此時也應該都在我道韻遮蔽之下,便如同天命雲子之能一般,令他也看不清、算不到。”
七百年來,終于盼到了這一日,阮慈長籲一口氣,只覺周身繩索略松了一些兒,對王真人也多了一點好臉,語氣放軟些許,道,“真人,徒兒此次前來求見,也是道途中有些不解,唯有請真人解惑。”
她還是只肯叫着真人,為自己幻成的繡墩,也在桌邊離王真人最遠的一角,王真人舉目盼來,說了聲,‘哦?’,倒是不見絲毫訝色,阮慈見他這樣,心中又生不喜,哼了一聲,方才将腰間人袋取下,往下一倒,道,“先要說起我這仆僮,說來也是奇怪,我在燕山救走他時,他已氣息奄奄,本以為他并不存生理,不知為何也就将其忘卻,自燕山歸來之際,并未将其送去救治,而是任由他在人袋中沉睡。出關時滿以為他大約已是隕落,誰知道神念一掃,卻發覺他有些古怪變化,還請師尊為我查看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