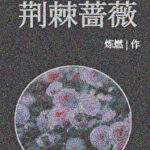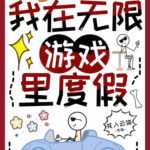“你怎麽也上來了?”荊笙兩條俊眉跟毛毛蟲似的扭在了一起。
神婆嘟嘴抱怨說,“嚴鳳那個小氣鬼,一口肉都不讓我吃!”
“那你就不要吃了!”荊笙玩笑說,接着他緩緩的推開了房門。這地方果然是別墅裏陰氣最盛的地方,一打開門,幾只幽魂惡鬼就從房間裏飛了出來,還好他們并沒有什麽法力,見到我們就四散逃走了。
而我則受不了這股子陰氣,覺得頭昏惡心就走出房門,給荊笙和神婆把風。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這段時間我是提心吊膽,生怕有人走過,把我們當賊給抓起來。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眼看着迎賓就要結束了,屆時白太太和秦歸海也該回酒席上了,我敲敲門板催促荊笙和神婆,“你們倒是快一點。”
說話間,荊笙已經打開門走了出來。
“怎麽樣?找到沒有?”我緊張的抓住荊笙的手。
荊笙似乎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于是他把目光投給了神婆,示意神婆回答,“沒在裏面。”神婆遺憾的說。
這下可真對不起秦慕了,我們沒能找到那孩子的魂魄,今天要是沒能找到就錯過了最好的時機了。
聽到樓下人群的哄鬧聲,悠揚的舞曲在宴會廳上萦繞揮灑,荊笙指着身旁好奇的問,“你不是伴娘嗎?這種時候你不見了肯定會引起衆人懷疑的!”
“我也沒辦法,要不你們把這鎖給鎖上!”神婆把弄着挂在門上的鎖,不耐煩的說,“這玩意鎖比開都難!不鎖好,不是讓秦歸海立馬就發現這房間有人出入過!你們先下去。”
“好,後面的事情交給你了。”說完荊笙就拉着我下樓了。
悠揚的舞曲傳來,白憲宗帶着嚴鳳在舞池裏邁開優雅的舞步,他臉上依然帶着不情不願,只是白憲宗太善良了,在這樣盛大的場面上,他不想讓衆人都下不來臺面,所以他不會把事情做得太難看的。嚴鳳的臉上噙着微笑,那嬌羞的模樣多迷人?修長的脖頸高傲的揚起,伴随這舞曲白色的婚紗劃過地面。看着她如今這副模樣,一定沒人會想象她真的是之前在妓院裏接客的人。
“我們也跳舞去吧。”荊笙拉着我的手帶我走進了舞池。
我慌亂的擺手拒絕,“我不會跳。”
白憲宗往我們這裏看了一眼,對上他的眼神竟然是帶着強烈的恨意,在行為上他并沒有表現出來,但是我太懂他了,他此刻的模樣殺意過盛,他恨我,可是他的殺意确實對着荊笙的。
我心虛的撇開了頭,不想看他,低低的把頭靠在荊笙的胸膛上。
“沒關系,我帶你,你放輕松就好了。”荊笙溫柔的在我耳邊說,他的氣息噴灑在我的臉頰上,癢癢的。
我擡頭茫然的看着荊笙,他緩緩的拉起我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摟住我的腰帶着我在舞池裏旋轉起舞。我們倆的舞步毫無章法,乍一看上去像兩個小孩子在舞池裏玩鬧,可是卻笑得那麽輕松惬意。
白太太神色凝重的望着我和荊笙,她握緊了拳頭抑制住自己的情緒,“這就是你說的那個和妖女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孩嗎?”白太太轉頭詢問陪在身邊的秦歸海。
秦歸海點了點頭,“就是她,但是她并沒有什麽法力,我當初叫兩人架着就把她扔進了小黑屋裏。”
白太太依舊目不轉睛的看着我,察覺到她的眼神,我十分的不自在,亂了舞步,踩了荊笙好幾下。
“放輕松,你若亂了陣腳才會讓人覺得奇怪。”荊笙咬着我的耳朵,輕聲提醒。
我羞紅了臉,責備荊笙都沒有力氣,“大庭廣衆的,你這是做什麽啊?”我推開荊笙嘟着嘴走出了舞池。離開之前,白憲宗的目光始終停留在我身上,他那麽難過,那麽恨,可是我不能幫他。
退到了一邊,我看着桌子上擺放了許多的點心和食物,想起了嚴鳳提醒我不要吃肉,擔心是肉裏有貓膩,我小心翼翼的攪動了盤子裏的烤肉,卻遭到荊笙的阻止。
“已經來不及了。”荊笙拉住我的手,眼裏透着厭惡,“他這招太兇殘了,也太令人惡心了。”
我還沒有弄清楚發生了什麽事情,就聽到人群裏爆發出一聲凄厲的尖叫。
“怎麽了?”跟着女賓的男賓,扶起了被吓得神志不清的女人。
女人指着自助餐點桌子上的鴻運金豬,捂着嘴顫抖了很久才說,“那肉裏有手指,是人的手指。”
障眼法被一個響指給打破,這動作快速得我來不及看清楚到底是誰解開的。障眼法一解除,人群裏就傳來各種各樣的哀嚎,以及幹嘔的聲音。剛剛還擺着烤乳豬的盤子裏哪裏還有什麽豬肉,豬頭的位置上擺着的分明是個人頭,全身通紅,被切成了小塊的樣子放在盤子裏任人食用。
我捂住了嘴巴,不讓自己尖叫起來,可是這場面太恐怖了,回過神來那些來賓都被吓得落荒而逃。我被吓傻了站在桌子前一動不動,荊笙趕緊沖了過來把我的頭按到懷中,“別看了,別看了。”
鼻尖萦繞着荊笙特有的書香味,這味道帶了魔法一樣,讓我很快就鎮定下來了。我不斷的在心裏對自己說,“你可是死過一次的人啊,現世裏的東西還有什麽能吓你?”漸漸的離開荊笙的懷抱,但還是因為恐懼攢緊了他的衣襟不肯放手,怯怯的回頭看了一眼餐盤裏的人,其實在看見她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了,她就是秦然。
“不要吃肉”我仿佛聽見了之前嚴鳳在我耳邊輕聲低語。她知道婚禮上會有這樣的一幕?
我猛然回頭尋找嚴鳳的蹤跡,以為她會趁亂逃跑,可是一回頭我看見她還是那般乖巧的模樣手裏莊重的捧着粉色的鮮花,聽聞,那是在婚禮結束之前要抛給參加婚宴的單身女青年的,接到捧花的人就能得到新娘的祝福,很快就能找到如意郎君。她蓋着蕾絲頭紗,透出她溫柔的笑容,笑着笑着,突然她把手中的捧花朝我扔了過來,花瓣飄灑飛揚了一路,紛飛而下如雪花般灑落,我鬼使神差的伸出了手,穩穩的接住了捧花。
“天靈,祝福你。”嚴鳳還在微笑,就像這婚禮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吃人事件,她依然在舉辦自己的終身大事。
不同于我們的淡定,身為父親的秦歸海看着那沒有人皮的頭顱,竟然只用了一眼就認出了被放在餐盤裏任人享用的是自己的女兒。
“啊啊……”秦歸海火冒三丈,怒不可遏的抽出麒麟頭拐杖裏的西洋劍,朝着嚴鳳揮下。
情緒波動那麽大,秦歸海的動作全都是破綻,嚴鳳輕巧的躲開了他看似兇猛的攻擊,她戲耍秦歸海一樣的和和他周旋,直到年邁的他沒有了力氣,只能靠在一邊大喘氣。
“你……你到底是誰?為什麽、為什麽這麽對待然然?”秦歸海上氣不接下氣的問。
嚴鳳傾着頭,平靜之中又帶着天真無知,她盯着秦歸海不解的問,“為什麽?為什麽只能允許你秦家吃人不吐骨頭,就不能讓衆人啃你們秦家的骨肉?”
這就是嚴鳳的問題,關于這個世界的不平等的疑問,她像個懵懂無知的孩子,一板一眼的要去探尋這個世界為什麽不公平的問題,過于真誠的眼神甚至看不到恨意。
秦歸海怒吼了一聲崩潰的癱坐在地上,他終于知道什麽是報應了嗎?
“你知道你們放火的時候我在哀求嗎?你聽到我的哭聲嗎?”嚴鳳噙着淚看着一個頹敗的仇人,她那麽善良并沒有趁機捅他兩刀,茫然的擡起頭,聲音平靜像是在訴說一個悠久的故事,“大火燒在臉上的時候有多痛你知道嗎?你的女兒衣食無憂的時候有多少人的女兒卻為了生計奔波,你買賣別人家的女兒,把她們送給那些高官禽獸糟蹋的時候可曾有過一絲一毫的內疚?你全家揮霍的分明是別人的命啊!”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一顆一顆的往下掉。
秦歸海不甘心的咬牙,撐着一口氣站了起來,“放屁!報應全都是給窮人的,沒有錢才是報應!”
原來還真是有人不見棺材不落淚啊,嚴鳳聳肩誇張的笑了起來,她用手背抹幹了眼淚,捂着眼睛笑得愈發的凄厲,“也對,跟你這種眼中只有錢的禽獸說什麽啊?”
秦歸海環顧四周見周圍的人都撤退了,他才深呼吸,準備使出自己的殺手锏。
“嗚啊,嗚啊……”一聲嬰兒的啼哭穿透整個別墅。
“鬼嬰!”荊笙說,“那一定是九姨太的孩子。”
“沒想到秦歸海居然敢用這種東西?”白太太的聲音從邊上幽幽的響起,我吓得躲到了荊笙的身後,把荊笙推向她。她怎麽還沒走啊?我不禁納悶。
白太太對我長相一直都挺好奇的,她很想知道我的身份,可是有荊笙障眼法的符紙在身上,她無法看到我任何的異常,所以此時在她眼裏,我就是個長得很若晴很像的尋常女子。
伴随着鬼嬰的出現,秦慕也跟瘋了一樣,從樓上沖了進來,其實今天他也趁着秦然的婚禮在秦家上下翻找婉兒的孩子。所以,剛剛的他并沒有發現會場裏有何騷動。
“這,這是婉兒的孩子嗎?”秦慕朝着鬼嬰伸出了手走了出去,這不僅僅是婉兒的孩子,還是他的孩子,雖然已經死了,可是能見上一面對秦慕來說都是一種天大的恩賜。